
南香红、梁鸿、袁凌在新书发布现场
2016年1月,非虚构作家、媒体人袁凌最新小说集《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非虚构写作成果丰富的袁凌,这次出版小说集《我们的命是那么土》,其中所选的大部分小说,是袁凌2005年回到家乡一年中陆续写下的故事。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2005年,袁凌在一家门户网站做新闻中心副总监兼主编。作为第一批转型去网站的媒体人,那是他职业生涯薪水最高、前景最光明的时期。“但是我灵魂非常的不安”,袁凌坦白,“我感到非常焦虑”。想要回到家乡的念头由来已久,家乡环境、包括人的急剧变化,让袁凌看到城镇化中乡土在发生亘古未有的断裂。
“不管怎样,那个地方养育了你,你应该去见证它,就算你做不了别的。”袁凌辞职,回到家乡,回到八仙镇乡下。开始写作这一本《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1月8日晚,在资深媒体人南香红主持下,袁凌和梁鸿在北京单向空间共同探索“土地与文字的边界”这一命题。
袁凌:当下怎么写乡村,怎么写农民?
当下怎么写乡村,怎么写农民?是不是还停留在鲁迅的写法,批判他们蒙昧的国民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基本就是愚昧、麻木、乱伦、肮脏这样一些特点,为什么会这样?袁凌把这些思考融入写作中。他认为如果作家在城市里写农民,可能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材料来运用。而正如梁鸿所说,农民是社会进程中的主体,而不是符号或静止的化石。所以袁凌力求写出活着的、有内心世界的农民。
小说名为《我们的命是这么土》,来自袁凌的一句诗“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只有两颗眼珠在转动”。袁凌认为,认为“土”不仅是书中人物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同时也是支撑乡村的本质。土不意味着肮脏落后,土是养育生命的,如果离开土就没有农民了。如果没有写劳动,就没有真的去写农民。另外,土也是自然的母亲,它养育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养育了节气、雨水、风俗,也养育了传说和神话,所以它确实是一个世界,但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肮脏落后的那种“土”,它像土层一样深厚丰富,甚至不乏生命的神奇。
袁凌认为自己小说不会很曲折充满了故事性和情节性,但却能打开一个世界,读者进入后会不停地看到很多东西。不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发生的各种小事,更主要的是他跟他周边环境的互动、互生性,在交换呼吸。袁凌希望自己写的东西不是一条封闭的巷子,读者进去之后被它的叙事带得没有办法选择,只能跟着它的逻辑往前走,最后只有一个可能的结局;他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一棵会呼吸的树,一棵故事树,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人物的故事没有办法跟周围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斩断联系。如果斩断联系,这个人的生命也就枯萎了。

袁凌
袁凌回忆,这部小说一开始的发表很不顺利,有十年左右没有刊登机会,被退稿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说你的语言很好,写得也很感人,但就是不像小说。“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在我耳边重复,”袁凌坦诚当时的受挫心,但他也一直用萧红的一句话——“为什么小说一定要照你们这么写?”来鼓励自己。他认为自己不是在写一个好看的故事,而是一个世界,一种生活和内心形态,这个世界需要进入,不是被人领进去,所以会有门槛,或者说有一点缓坡。
一般的小说都强调人性,觉得小说把人性的复杂写出来就够了,譬如托尔斯泰所说人性的辩证法。袁凌认为这过于简单化了,人性很虚,人性受到物性的规定和限制。袁凌希望自己的小说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人性,还有“物性”,因为人在世界上生活,受到他生长的环境、生活的、物质的影响。人性处于神性和物性之间。
梁鸿:“土”是一种世界观
梁鸿表示自己是袁凌的忠实读者,从《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到最新的《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她一直非常喜欢袁凌的文字。梁鸿认为《我们的命是那么土》跟袁凌之前的几本书完全不一样。前者是散文的形式的非虚构纪实,基于真实的场景人名、地名,而《我们的命是那么土》已经略微脱离了文学层面的“真实”层面。
梁鸿认为尽管书写的对象是古老的土地和乡村,但袁凌的文本姿态并非是一个传统的写作者,他的语言是对现代汉语非常好的表达。同时这种写作展示出袁凌对世界毫发毕现的观察,他能看得清晰,也能够叙述出。他对人的观察、对生活的观察非常细致,他能从火车站外一张破旧的、差点被风吹走的寻人启事,寻找到一个生命的痕迹,并且追寻下去。梁鸿认为这非常了不起。所以袁凌是一个有悟性的作家。并且因为他有扎实的现实经验,有扎实的现实书写能力,他的小说书写能够做到既有飞翔的层面,又有落地的可能,能够让你触摸到它的重,同时又有轻的成分。这样一种轻呢,不是一种轻灵、语言优美之类,而是能够让你感知到它所表达的世界之外的世界,世界观之外的世界观,这是轻的方面。重的方面又是跟现实相关。读袁凌的非虚构作品,自己能看到一种特别沉重的现实,特别扎实的现实的细节,袁凌是完全进入到这个人物的世界里面,这是轻与重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既是现实的,也是美学层面的一个存在。
所以人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土”并不符合袁凌的作品的,他不是在写我们印象里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也不只是在写苦难,虽然那种生活的确很苦,但读者能看出里面的审美来。这种苦难里面有很大的美感,因为有生机。
梁鸿从袁凌创作轨迹分析,认为袁凌一直在关注 “重”生活,不管是写矿工,还是《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每一种死亡都是一次生命,让人在有痛感的同时感到珍惜。让人珍惜的还有袁凌的文字,他把每一个生命印刻在了文字当中。除了人和动物,还包括物的生命。
在小说集《我们的命是那么土》,袁凌不仅蕴含了自己对乡村的看法,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书写写出了不一样的普通人。而袁凌文字的细密显示出不单单是对外在现实事物的把握能力,他确实是安静的把握者,一个心静如水的人。
袁凌小说的意义不在于感叹,而是在于发现,试图给我们呈现一个更加丰富细微的乡村,更加富于血和肉的人类的生命形态,不单单局限于乡村。
【书籍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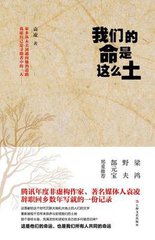
书名: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作者: 袁凌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1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这是袁凌的家乡,也是这部小说集中每个人生活的地方。他们当中有在煤矿事故中失去眼睛,一身伤痛地回到家乡的中年人;有一身旺盛青春在大山深处犹如困兽的年轻男人;有出国打工染上艾滋病客死异乡的年轻女人;也有翻越大山只为打一个电话给自己安排后事的老婆婆……这些故事来自土地,也终将被埋入土地,而袁凌用深情而克制的文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使之得以被见证。
这样的乡村在当下中国并不罕见,这片土地曾经丰沛鲜明而神奇,而现在,它黯淡、受损、贫瘠,但几千年以来至今,这片土地依然在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庇护与慰藉,也在为看似遥远的城市文明提供生存根基——如同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乡。而那些人,他们沉默地挣扎着、卑微地祈求着、也郑重地感激着,他们不乏尊严,正如那些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
我们需要一支犀利的笔写下中国乡村现状,我们更需要这样充满温度与细节的文字带我们重新回到乡村,重新认识土地上的人们。因为家乡从未真正关闭通向她的道路,认识他们,也是认识我们自己,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命运。
愿我们都成为寻路者中的一人。
作者简介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知名记者,曾发表有影响力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多篇,代表作《走出马三家》和《守夜人高华》获得2012、2013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暨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南方周末》和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在《小说界》《作家》《天涯》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书。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新浪2014年度好书榜入围,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 袁凌,1973年生于陕西平利。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知名记者,曾发表有影响力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多篇,代表作《走出马三家》和《守夜人高华》获得2012、2013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暨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南方周末》和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在《小说界》《作家》《天涯》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从出生地开始》等书。腾讯书院文学奖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新浪2014年度好书榜入围,归园雅集2014年度散文奖。
责任编辑:何妹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