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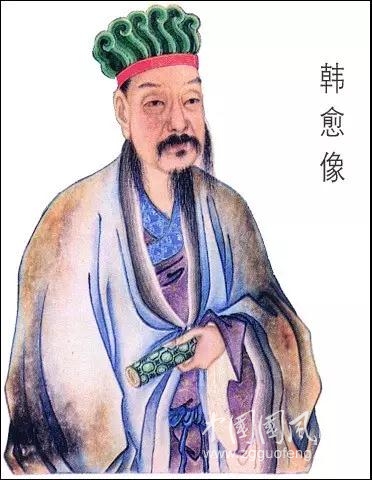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官至吏部侍郎,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毁誉参半的德操品行
韩愈为人,毁誉参半。韩愈向以儒家正统自居,其实他的思想却很驳杂,行举也往往前后矛盾。他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也反对神权迷信,但又信鬼神尊天命;他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宗孔氏,贵王道,而又崇管仲、事商鞅;他立场比较保守,指斥革新派是“群小用事”,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重大问题上,又旗帜鲜明。诚如苏轼批评他“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韩愈的品行,基本上是属于优秀的,或者说,韩愈有许多的优秀品德,譬如,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等,但是,也有比较突出的问题。他品性中的这些低劣方面,我们从他贬连州阳山令、“二王八司马”事件等几桩历史公案,便可很清晰地看出。
舒芜先生在为《韩愈诗选》所作的序中说:“通观韩愈这个人,尽管是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但是气质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躁急褊狭,无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别热衷利禄,无恬退之心。他的诗篇当中,经常贬低朋友,好为人师,攘斥异端,自居正学,就是褊狭的表现……谁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贵,谁不尊敬他的学问文章,他对谁就会恨之次骨,永世不忘。”
他接着说:“这样的人的精神状态中,自然容易充满了怨毒之气,怨毒之极又自然通于杀气。贞元十九年,韩愈因建言被贬斥,这一段经历他在诗中再三再四地说起,对于政敌王叔文集团,包括对老朋友柳宗元、刘禹锡,真是悻悻之状如见,切齿之声可闻。待到王叔文失败,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司马”一时窜逐,韩愈这时便写出了幸灾乐祸、投井下石的《永贞行》。”
因此,“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上的庸俗性,总带有独断和专制主义的味道”。舒芜先生之语真有点不留情面的尖刻,似乎也不是场合,却也字字有根。孙昌武先生对韩愈在“永贞革新”的态度颇为不满,他说:“由于人事的、性格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原因,韩愈却站到了革新派的反面。按他的缓进的、比较保守的立场,革新派是‘群小用事’,窃夺国柄。他因此被革新派排斥并被流贬岭南。在以后的诗文中他对革新派一再大张挞伐。这成了他一生活动中的阴影。”关于韩愈“永贞革新”的态度,论者多甚,毋庸赘言。我们以为,韩愈被贬潮州前后的表现,也是很能够看其思想品格的。
“谏迎佛骨”事件
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掀起信佛狂潮,韩愈毅然上书《谏佛骨表》云: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措辞激烈,出言无忌,极言辟佛之由,以历朝佞佛皇帝“运祚不长”来推论,结论寓于其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宪宗得表,龙颜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韩愈你也太过分了,奉侍佛教的皇帝都是短命的,你是说我也是短命的了。作为人臣,狂妄之极!” 宪宗要处韩愈以极刑。幸得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竭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往潮州的途上,写下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诗中表现出坚强的斗争意志:“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然对照其贬官潮州后,遽惴惴恐道死而乞灵湘江女鬼等行举,则判若两人。
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反反复复申言的几层意思:其一,臣冒犯天威,“万死犹轻”;“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其二,臣“忧惶惭悸,死亡无日”,万望“陛下哀而念之”,如果陛下不可怜我就没有人可怜我了。其三,陛下“巍巍之治功”,诚当“纪泰山之封”,而臣则是最佳的作颂之人,“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胡适博士在《白话文学史》里分析韩愈谏佛骨前后过程而探索其患得患失的心理时指出:“当他谏佛骨时,气概勇往,令人敬爱。遭了挫折之后,他的勇气销磨了,变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他在潮州时,上表谢恩,自述能作歌颂皇帝功德的文章,‘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并劝皇帝定乐章,告神明,封禅泰山,奏功皇天!这已是很可鄙了。他在潮州任内,还造出作文祭鳄鱼,鳄鱼为他远徙六十里的神话,这更可鄙了。”细观韩愈此表,再联系他上表前后的许多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看,就更加会发现,韩愈的《谏佛骨表》似乎有一种故作惊世骇俗语的嫌疑,其上表谏迎也就并非那么的高尚了。也可能真是被他的悔改之意所感动,陛下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将贬官只有八个月的韩愈召回京城而予以重用也。
“谀墓”问题
韩愈写了大量的墓志,人道是“谀墓文”。 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不无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李泽厚更是在此问题上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认为他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
除记功碑《平淮西碑》和庙碑《处州孔子庙碑》《黄陵庙碑》《南海神庙碑》《衢州徐偃王庙碑》外,韩愈计有碑志七十五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以重金来求韩愈写墓志,连那个给杜甫写墓志而让杜甫立时爆得大名的高官元稹,其妻子韦丛的墓志也请韩愈来写?这也足证,韩愈在当时文坛乃至整个社会上的影响非同一般。不少学者认为,韩愈大量写作墓志,是为窘迫经济所迫。他自己就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包括侄子韩老成一家,据说已经“家累三十口”。据说韩愈有个账本,日常收支皆有账目,其中有两个收费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收王用男人“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而在韩弘处得“绢五百匹”。马和腰带是什么价钱现在无法计算,但一匹绢当时“直钱八百”。韩愈为国子博士时的月薪约二十五贯。那么五百匹绢就是四百贯钱,等于他月俸的十六倍。中唐时期,一斤盐的价钱是四十文,一斗米是五十文,按照当时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约七石二斗计,这四百贯钱大约够一百人一年的口粮。只要写一个碑铭,就能得到一笔不小的财富。韩愈多写墓志,为了生计,情有可原。
我们则不这样看,“谀墓”非原则问题,未必构成韩愈的道德品质上的缺陷。
其一,撰写墓志而收费非始于韩愈,也非韩愈一人所为,在唐代各个时期的其他文誉卓著的高官中,为人写墓志而收取钱财的多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其它的撰写,有润笔费可收,为什么撰写墓志就不能收费?完全可撇开韩愈的家境不谈,如果他极富有,收费也不为过。以我们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来看,谁都会觉得韩愈收费情理之中。
其二,从墓志的文体看,称善而隐恶也没有错。刘勰的《文心雕龙》里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也就是说,除了要叙述往者的生平事迹乃至籍贯世系外,还要陪上歌功颂德的铭文。曾巩认为,铭志只书善不书恶,但是,书善要做到“公与是”。何为“谀墓”?《辞海》的解释是,“为人作墓志称誉不实”。如果在墓志中,做“不实”性的评判或称颂,是为“谀墓”。只要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不是颠倒黑白的瞎编,不是指鹿为马的胡诌,而适度渲染、合理加工、精心构思、精巧措辞地拔高,称善而不显恶,说点适度“好话”,似乎不能叫做“谀”。也不是为韩愈开脱,以韩愈的人品考,应该不存在主观上的谀墓动机的。
韩愈志在做一个“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答李翊书》)的正人君子。应该说,在唐代文人中,韩愈确实算得上综合素质、道德水准很高的。苏轼说他内外兼修、文武俱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也是很实事求是的评价而非“谀墓”之言也。而其“利禄情深,恩仇念重”(舒芜语),则是引发其弊行病举的性格缺陷和思想根源。
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韩愈自命不凡,具有过高的以拯时救弊为己任的期待,自比儒家道统最合适之传人。他性格狷介强梗,争奇好胜,不安凡庸,极具挑战性。韩愈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躁急褊狭,特别热衷利禄。韩愈诗极富争议,乃诗中之别调,以文法而摧破诗法,将以功力为诗的写法推向极致,刻意奇崛,终成自己面貌,成为审美异化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代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韩愈诗风险怪,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姿态横生,变怪百出,赋予诗歌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即便这种诗歌因追求新奇过甚,产生了怪诞晦涩的负面影响,而韩愈的独创精神,新变自觉,以及这种精神所生成的不俗的表现,则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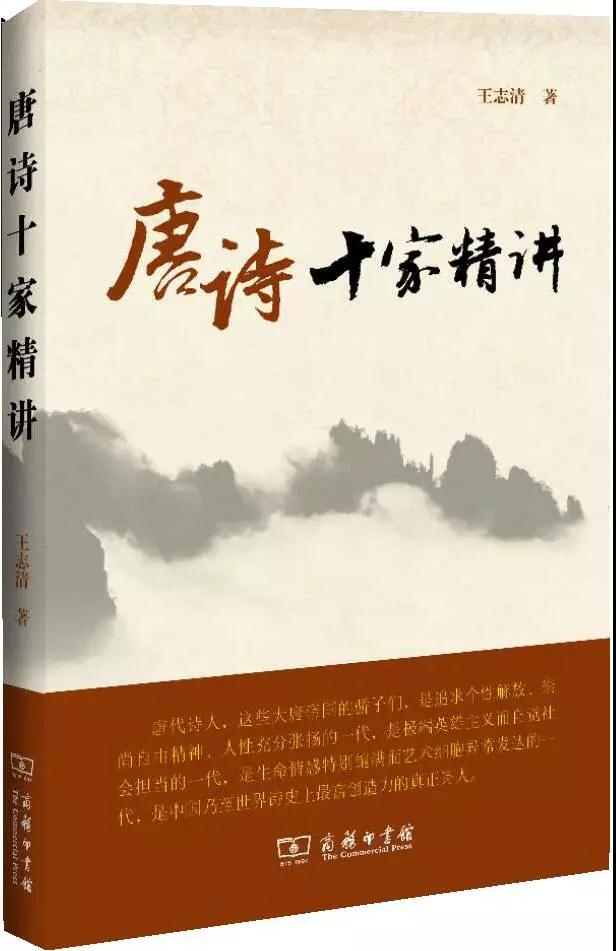
王志清先生著作

王志清先生
【作者介绍】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等,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关于王维研究的文章40多篇,代表作有《纵横论王维》《王维诗选》《王维诗传》《唐诗十家精讲》《盛唐诗学》等。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