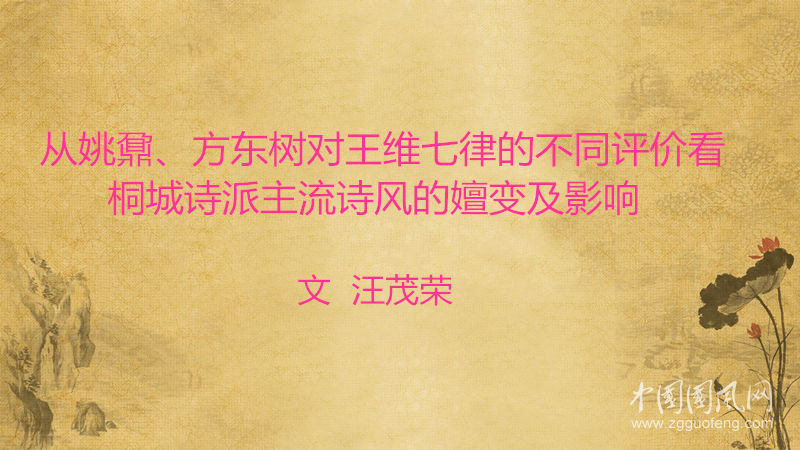
桐城诗派是产生于清代中期(雍正、乾隆年间)的一著名诗歌流派。因创始时期的几位核心人物姚范、姚鼐、方东树均来自于桐城,故派以地名,被称之为桐城诗派。在清代文学史上,其影响之大虽不及桐城文派,但亦不应低估,晚清以降,程秉钊、曾国藩、沈曾植、钱基博、钱仲联等著名学者对之均有较高评价,钱锺书甚至认为桐城之诗实胜于桐城之文。
这些名家对桐城诗派给以如此高的评价,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应与桐城诗派在清代诗坛主流诗风嬗变过程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有关。众所周知,清代前期诗坛的主流诗风为唐风——代表为神韵派、格调派,清代后期诗坛的主流诗风为宋风——代表为前期宋诗派、后期宋诗派(同光体),而在推动前期唐风向后期宋风嬗变的过程中,崛起于清中期的桐城诗派即承前启后,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认定桐城诗派是为诗坛宋风取代唐风这一大因缘而生,虽不中亦不远。
那么,桐城诗派在清诗前期主流诗风唐风向后期主流诗风宋风嬗变过程中是如何起到这种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得了解推动并承载这种变化的桐城诗派本身的主流诗风是如何嬗变的。我们知道,桐城诗派的重要理论之一,即是“熔铸唐宋”(《见惜抱轩尺牍·与鲍双五札》)、“由模拟以成真诣”(见欧阳功甫《秋声馆遗集·与罗秋浦书》记梅伯言论诗语)。但“熔铸唐宋“是笼统说的,具体到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其侧重于唐风抑或侧重于宋风,还是皦然有别的。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选择一个小的切入口,以姚鼐、方东树对王维七律的不同评价为例,来看看桐城诗派的主流诗风是如何逐渐地由唐风向宋风嬗变的。
先看看姚鼐是怎样评价王维七律的:
右丞七律,能备三十二相而意兴超远,有虽对荣观,燕然超处之意,宜独冠盛唐诸公。于麟以东川
配之,此一人私好,非公论也。
——《五七言今体诗抄序目》
桐城诗派曾把唐诗中的七律分成两派,两派各有一祖,一祖为王维,一祖为杜甫。尽管各为一祖,但由这段话可见,被姚鼐许为“独冠盛唐诸公“的为王维,非杜甫,扬抑如此,于王维评价不可谓不高。而这个评价的本质,则反映了主张熔铸唐宋的姚鼐在具体的审美取向上是将尊唐置于尊宋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牵涉到什么叫唐诗,什么叫宋诗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分析得很清楚:
唐诗、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
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
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
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夫人秉性,多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
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然而然者。
由钱先生分析可知,杜甫虽是唐人,但杜诗在唐诗中只能算是别调,非正宗,唐人选唐诗,甚至有不选杜诗的,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就是。杜诗被奉作正宗的,反而是在宋代。故宋人大多重杜,历来学宋者也大多将杜当作是宋法的代表而加以取法。姚鼐的看法实际也是如此。他认为:“杜公七律,含天地之元气,包古今之正变,不可以律缚,亦不以盛唐限者。”(《五七言今体诗抄序目》)所谓包古今正变者,实指杜甫七律已包含有宋诗的元素在内,用唐诗的标准来衡量,杜甫七律博大则有之,但并不精纯。有鉴于此,姚鼐将杜甫的七律视为唐诗别调,而特别推崇王维的七律为“独冠盛唐诸公”,就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同时就具体取法学习来说,姚鼐对王维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杜甫。这种重视甚至延伸到了后来的学王者,如对明七子、清代的王渔洋,他都比较重视,认为“吾以为学诗,不从明李、何、王、李路入,终不深入”(《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论诗如渔洋之《古诗抄》,可谓当人心之大公者也。……要其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道启后进”(《五七言今体诗抄序目》)。其七律就是借“七子”尤其是李攀龙以学习王维的。但为了避免“七子”学唐流于肤廓的毛病,他同时又强调学宋尤其是学山谷,力图以宋人的筋骨思理来对治七子的肤廓。郭频伽在《樗园销夏录》中曾说:“吾师姚姬传先生曰:‘近日为诗,当先学七子,得其典雅严重,但勿沿习皮毛,使人生厌,复参以宋人坡谷诸家。”可见姚鼐所作七律实际是熔铸唐宋而成。虽是熔铸唐宋而成,但由于取法有所侧重于唐尤其是王维,其总体风格还是唐风多于宋风的。不妨选几首以为欣赏:
岳州城上
高接云霄下石矶,城头终日敞清晖。
孤筇落照同千里,白水青天各四围。
山自衡阳皆北向,雁过江外更南飞。
人间好景湘波上,却照新生白发归。
望潜山
道边只堠复双堠,天半大山宫小山。
客子出村暮唤渡,居人微雨寒闭关。
橫空积树云漠漠,交流断径溪潺潺。
不知苍松最深处,乔公白鹤谁往还。
金陵晓发
湖海茫茫晓未发,风烟漠漠棹还闻。
连宵雪压横江水,半壁山腾建业云。
春气卧龙将跋浪,寒天断雁不成群。
乘潮鼓楫离淮口,击剑悲歌下海濆。
夜起岳阳楼见月
高楼深夜静秋空,荡荡江湖积气通。
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
云间朱鸟峰何处,水上苍龙瑟未终。
便欲拂衣琼岛外,止留清啸落江东。
过汶上吊王彥章
杨刘兵渡大梁危,饮泣犹当奋一麾。
乱世鸟飞难择木,男儿豹死总留皮。
天连白草横残垒,日落阴风拥大旗。
莫问夹河争战地,浑流徙去黍离离。
雄县咏周世宗
世宗北伐志犹勤,山后宁容地剖分。
天意自留耶律氏,人心俄变殿前军。
五朝庶见真神武,再世何难嗣守文。
反覆兴亡无处问,瓦桥关外又斜曛。
登永济寺阁是中山王旧园
中山王亦起临濠,万马中原返节旄。
坊第大功酬上将,江天小阁坐人豪。
绮罗昔有岩花见,钟磬今流石殿高。
凭槛碧云飞鸟外,夕阳天压广陵涛。
这些七律,高振唐音,调逸气舒,句浑音圆,的得盛唐尤其是王维七律法乳。与同学王的李攀龙、王渔洋比,姚氏七律既避免了前者的高调肤廓、神理蔑如,又不似后者的一味清秀、气寒力怯,其故何在?其故就在于他在主学盛唐的同时,还兼学宋人尤其是山谷,以宋人尤其是山谷的筋骨思理以对治李、王诸人学唐所易犯的“虚车”之病,可谓对症下药,起死回生。姚鼐的门生姚莹评其师“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识小录》),当为深中肯綮之论,虽然姚鼐七律于宋取法的主要对象为山谷而非坡公。由此可见,姚鼐的七律虽以盛唐尤其是王维的七律来立体,但亦不废兼学宋人。从本质意义上说,姚鼐所代表的桐城诗派主流诗风唐风实是承清初以降王渔洋、沈德潜等人学唐之风而来,并兼学宋人以弥缝其阙而底于成的。若进一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则兼学宋人在当时还是一种新风气,而这种新风气由姚鼐这样一位名家来提倡,必将使诗坛产生一种见贤思齐、向风成会的学习效应,从而极大推动了桐城诗派主流诗风的嬗变,即由亁、嘉时期的以唐风而为主逐渐转向嘉、道时期的以宋风为主。
再来看东树是怎样评价王维七律的:
(按:此处指王维七律),亦称一祖。然比之杜公,真如维摩之于如来,确然别为一派。寻其所至,只是以兴象超远,浑然元气,为后人所莫及;高华精警,极声色之宗,而不落人间声色,所以可贵。然余乃不喜之,以其无血气性情也。譬如绛阙仙官,非不尊贵,而于世无益;又如画工,图写逼肖,终非实物,何以用之?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政如司马相如之文,使世间无此,殊无所损,但以资于馆阁词人,醖酿句法, 以为应制之用,诚为好手耳。
——《昭昧詹言》卷十六
所评虽高度肯定了王维七律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但尊而不亲,认为王作七律“无血气无性情”,直言“乃不喜之”。王维七律代表的是唐风的正宗,不喜代表唐风正宗的王维七律,表明方氏必另有所宗。根据相关资料考察可知,方氏所宗的乃是具有宋风倾向的杜甫七律和宋人黃山谷的七律。且看他的自述:山谷之学杜,绝去形摹,尽洗面目,全在作用,意匠经营,善学得体,古今一人而已。
欲知黃诗,须先知杜;真能知杜,则知黃矣。杜七律所以横绝诸家,只是沈著顿挫,恣肆变化,阳
开阴合,不可方物。山谷之学,专在此等处,所谓作用。义山之学,在句法气格。空同专在形貌。三
人之中,以山谷为最,此定论矣。
——《昭昧詹言》卷二十
所论虽不薄唐人,但尊而且亲的对象已完全转换成宋风。且方氏对于宋风不独可坐而论道,还进而能起而行之。不妨略举几首其所作七律以为印证:
寄姚石甫观察台湾
经济槃槃仰大才,天心笃倚障澎台。
柙中兕虎关机伏,海上鲸鲵詟气回。
畺理周家维召翰,楼船汉将纪杨推。
良书一卷参微管,怅望嗟乖缨弁陪。
马公实幼白兄弟于其先垄玉屏山兰若旁新构山楹
丙舍各一区于时享祀于时游眺为题一诗兼示元伯
玉屏兰若亚连岗,更缭周墙启榭堂。
伏腊岁时承祀远,丹楹刻桷照山光。
见看野水平畴白,即想秋林落叶黃。
判拟同君返遥夜,云岩迴望月苍苍。
乙巳九月张佑孚招游龙眠双溪
十至龙眠未有诗,藏胸久负许多奇。
清时宰相归来早,名士山庄在处疑。
白首莳松鳞尽长,青云临氵片翼犹垂。
何人为貌同游侣,全仿山阴继伯时。
奉寄姬传先生
当年杞梓遍龙门,高弟传经世并尊。
再世彭宣同入室,众中王粲倍衔恩。
雠编尽付风前叶,步屧曾偕江上村。
十载豫章曾不辨,漫看樗散自乾坤。
寄刘孟涂
西京奇气今时少,南浦相思别后增。
埋剑丰城仍未出,为云东野讵同升。
路难天地双鸿爪,岁暮江湖一客镫。
莫道愁怀难独醒,百壶且试酒如渑。
诸诗于杜、黃皆有取有舍,于杜逊其沈郁而有其顿挫,于黃去其槎丫而有其典雅,虽融唐宋于一炉,而神明变化,究以得之于宋人者为多。同乃师姚鼐比,如果说姚之七律主要是以唐风立体的话,那么时过境迁,方东树已过渡为以宋风立体了。姚、方是桐城诗派不同时段的代表人物,姚、方诗风的嬗变从本质上反映了桐城诗派已完成了其主流诗风的嬗变,即由唐风向宋风的嬗变。而完成这种主流诗风的嬗变对晚清以降的诗坛影响是巨大的。在这当中,方东树的作用尤其不能低估。作为完成这种嬗变的核心人物,方东树不独创作成绩斐然,理论上亦卓有建树。其中最突出的是著了一部《昭昧詹言》。作为一部诗学鉴赏名著,《昭昧詹言》处处体现着桐城诗派的“家法”。特别是在体式上,此书就王渔洋《古诗选》和姚惜抱《今体诗抄》所选的诗,驾轻就熟地运用桐城古文家所擅长的评点之学,首首加以批注,诗律文心,挟发无遗;金针度世,沾溉广博。正是得力于方东树等人的大力宣传,道、咸以后的前期宋诗派(代表人物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后期宋诗派(即同光体,代表人物为陈三立、郑孝胥、陈衍)才承桐城派遗绪,先后继起,而终使宋风成为晚清至民初诗坛的主流诗风的。(关于桐城诗派与前、后期宋诗派之间的关系,可参看拙撰《论桐城诗派》一文)
综上所论可知,作为桐城诗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姚鼐、方东树虽均主张熔铸唐宋,但在对待王维问题上,两人又略有不同。姚鼐对王维是尊而且亲的,故其七律虽亦兼学杜、黃,但大端还是学王并以王立体的,风格上更多体现的是唐风。方东树对王维则尊而不亲,其七律亦刻意规避王维这一路,而大段取法杜、黃并以宋人立体,风格上更多体现的是宋风。姚、方是桐城诗派在不同时段的代表人物,姚、方诗风由唐风向宋风的嬗变实际上显示的是桐城诗派主流诗风由唐风向宋风的嬗变。而这种嬗变对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在清朝前期诗坛的主流诗风是唐风;清朝后期,诗坛的主流诗风是宋风。崛起于清中期的桐城诗派适当其会,通过“熔铸唐宋”承前启后,并凭藉其自身诗风的嬗变和巨大的影响力,推动诗坛完成了主流诗风由唐风向宋风的嬗变,顿使生面别开,奇境独辟,一洗凡猥。研究清代诗史,桐城诗派的这一贡献当是功不可没,值得大书特书的!、
2017.10

汪茂荣先生
【作者简介】汪茂荣,男,1962年生,安徽省桐城市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学高级教师。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持社社员、中华诗词(BVI)研究院特约编辑、“诗教网”第二届国诗大赛评委、安徽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理事、“安徽省近百年名家诗词别集丛书”编委、桐城市书法家协会学术顾问、桐城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桐城诗词》主编。著有《懋躬丛稿》,点校出版《睫闇诗抄》、《周弃子先生集》、《海外庐诗》、《诗法通微》、《坚白精舍诗集》、《周退密诗文集》、《唐玉虬诗文集》(后二种与刘梦芙教授合作。以上各书均由黄山书社出版)。主编《安徽桐西汪氏宗谱》。“汪茂荣旧体诗选”获《诗潮》杂志社2013年“最受读者喜爱的诗歌奖”年度金奖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