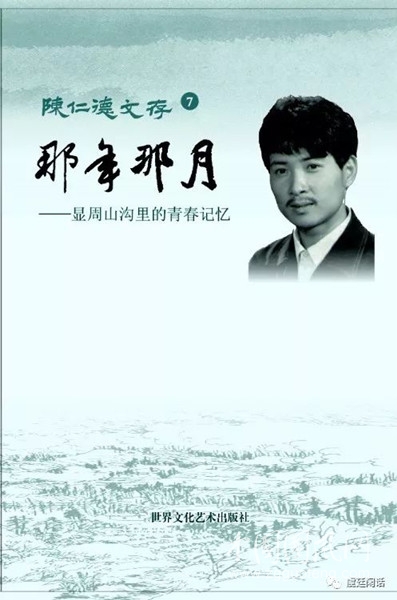
【10】风雨中穿越80里崎岖山路
1976年夏天,曹邦梅调到了更远的地方——三汇区泰来完小。当时我写有一首《菩萨蛮•山中》:
故关望断无音讯,
山中日日西风紧。
谁能与销愁,
飘摇春复秋。
情人驱远道,
仰视浮云渺。
无事且安眠,
梦中别有天。
年底,我和曹邦梅办理了结婚手续。
我和曹邦梅工作的泰来相隔80里山路,那80里山路全在崇山峻岭之间,其中有许许多多险沟深壑悬崖峭壁,有的地方几乎没有人烟。要想相聚,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必须翻山越岭,依次走过显周、花桥、马灌、黄龙、泰来五个公社。如果想不走路,就必须第一天徒步到拔山去乘客车进城,第二天从县城乘车到三汇,再徒步30里,来回在路上就要4天,而我的假期最多就是四天。我只能选择走路。
说来我自己现在都不相信了,那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山古道,我居然创造过五小时走完全程的记录,真不知当时怎么竟有飞毛腿一般的功夫。
其实阻碍我的主要不是那条可怕的山路,而是当时十分苛严的请假制度。我是营业员,不能随便关门,关了门农民就买不到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也是不能请假的,好不容易请一次假都要间隔两月以上,而且假期最多四天。之所以四天,是因为那时乡下是五天一场,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必须在下一次赶场前回来开门营业,除了在路上往返奔跑,我实际在泰来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
请假必须提前几天打报告,一旦获得潘经理恩准,我就高兴万分,天天焦急地等着那个日子。到了那一天,匆匆收拾好行装,象野马一样嗖的一下就溜了出去,一会儿就翻过了一座山。
起先由于不识路径,不知在荒山野岭中多少次迷路。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印着兽迹的一片片乱山坡,翘首四望,连人烟都没有,就只好凭感觉乱闯。走了好久好久,终于看见了院落,赶紧向人打听,才知道走到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了,只好独自长叹一声折回重走。
道路虽然崎岖曲折,可是深山里人迹罕至的地方却有着绝美的风景。幽深的山谷里,小溪潺潺地奔流,满山的野草郁郁葱葱,不知名的鸟儿在悠闲地歌唱着,巍峨的悬岩从四面合拢来,人好象行走在井底。累了,就仰卧在那些洁净无尘的青石上,望着朵朵白云从高高的山顶上飘过,感觉惬意极了。
最难过的是两天后的返程。体力还没恢复又得重新踏上那条道路,心里实在是不情愿。由于无论如何都得赶回开门营业,所以即使雷电交加,也得冒险上路。说来也实在不凑巧,我十有七八都是冒着风雨踏上归程的。
临出门时,曹总会把一把雨伞塞到我手里,然后去找来一把稻草,俯下身将稻草挽在我鞋上,双手使劲地搓,直到将稻草搓成一根结结实实的指头粗的草绳,再将草绳反复缠在我鞋上——这叫“草脚马”,是山区农民雨天防滑的一种特有方式,这样,我就可以出门了。
撑开伞,最后一次回望站在屋檐下的曹,转身就走进了满天雨幕。再回首时,一切都已消失在如丝的乱雨中。
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啊,满山的山洪爆发了,平常十分温柔的潺潺流水忽然象野兽一样咆哮起来,山洪从高处飞奔而下,浑黄的溪水在岩石上摔得粉碎,发出雷鸣般的声音,震得整个山谷隆隆作响,许多小路都已被山洪淹没,没有淹没的也大多成了烂泥。而我,一个孤独的深山行客,却要迎着山洪一直往前走。
小小的雨伞挡不住满天风雨,没多久,身上就浸满了雨水,肌肤一阵发冷,但随着体力的消耗,全身开始冒汗,却又开始发起热来。脚下的“草脚马”每走一步,就在泥地上印下两道绳痕,鞋子里早就灌满了泥浆。
也不知走了多久,肚子饿了,却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低头看脚,两只“草脚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踪影——早就磨掉了。
就这样一路风雨一路泥泞走完80里山路,来不及休息,又得准备第二天的工作了。
【11】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曾发生过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一次,我到了泰来完小,学校里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老教师硬要请我们去他家做客,说是早就准备好了,他家就在学校附近几里的地方,去来很方便。我一再谢绝,那位老教师却铁了心非要请我去不可,边说就边来拉我。
我看看天色还早,反正路也不远,就只好与曹一道去了,心里打算的是在天黑前赶回学校来。
到了老教师家里,他马上吩咐他老婆做饭,又是煮腊肉,又是推豆花,搞得热气腾腾。一会儿院子里的农民听说来了客,都过来围着我们话家常。
我看这样子一时可能吃不成饭,天黑前能否赶回去很难说,就悄悄和曹商量好,婉谢主人的好意,我们必须回学校去。谁知我刚开口,主人立马笑着打断我说:“什么事不可以明天做?今天就安心住下来,不要客气嘛。这样吧,我拉二胡给你们听”说着果然转身从里屋拿出一把破二胡来,用嘴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就吱嘎吱嘎地拉起来,原来是一支老曲子“绣金匾”,听起来咿咿呀呀,所有音都是跑调的。
我哪里听得进去“绣金匾”,又哪里有心思吃他的饭。趁他“绣金匾”入了神,我和曹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就假装散步偷偷溜出了门——没办法,我们只好“私奔”了。我们轻轻地从院子旁的竹林穿过,往下山的路快步走去,心里才算轻松了些。
刚转过一个山坡,忽见前面窄窄的小路上站着一个人,那人冲着我们哈哈大笑,说:“不要走!”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老教师,原来他发现我们“私奔”后抄近路来拦截我们了,顿时我们的心一下揪紧,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我们乖乖地被“押”了回去,晚上吃腊肉豆花,满满一大桌农家菜,院子里几位长者都被请来陪我喝酒,屋子里洋溢着喜气,我也只好强打起笑脸,陪他们说一些言不由衷的空话。酒足饭饱后,老教师安排我和他抵足而眠。
第十四章 路线教育
【1】工作组来了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大搞阶级斗争,在“学好文件抓住纲,狠揭猛批四人帮”的口号声中,当年初冬时节,又一轮政治运动开始了。这次的运动叫“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对于“基本路线教育运动”这个名词,后来的人们可能看不懂,需要简单诠释一番。按照正规的说法,基本路线是指共产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指导全局的总任务、总方针、总政策的集中概括,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是一定历史时期全部实践的指南和依据。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基本路线是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谁敢说半个不字,便是逆天大罪。从六十年代起,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表述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基本路线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大搞斗争。专门以基本路线为教育内容进行的运动,就是“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了。十多年来,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已经反复开展了很多次,每次都是腥风血雨,整人害人。
和1973年的“三分之一”运动一样,也是工作团进驻到公社,下分若干工作组到各生产大队。略有不同的是,此次增设了一个机关工作组,专门对社属“八大单位”进行基本路线教育。进驻公社的工作团团长是县劳动局局长古之涛,秘书长是统战部古之玉。和我有直接关系的是机关工作组,组长是县财政局股长陈志忠,40多岁,副组长是县粮食局股长祝裕华、成员是县交通局崔太奇,朱和崔都30多岁。
工作组照例是每天晚上占用职工的休息时间组织学习文件,地点在诊所候诊室里。那正是江青一伙被关押——习惯称为“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接连不断的揭露四人帮的材料发下来。就是那些材料使我们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中央高层内幕。比如华国锋讲,江青一个月八万元还不够花——这令我们惊讶,那时月工资只有30元左右,年工资加在一起也只有360元左右。100年工资也不过36000元。江青一月所花的钱,我们要200多年才能挣到。材料里又说,江青去山西大寨大队视察时,开了一个专列,连她的沙发厕所都带了去。江青是30年代上海的戏子,名叫蓝萍,作风败坏,曾经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江青企图谋害毛泽东,毛泽东病重时,她不听医生告诫,强行给毛泽东翻身,导致血压迅速上升发生严重危险等等。这些揭露四人帮的材料都是中央发出的,据说由于泄露了某些秘密后来都收回了。
工作组要求每个人都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就像不久前批判邓小平一样。这对我毫无问题,随手就按照通行的“八股”形式写了。而其他一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人就恼火了。召开评判大会时,要求每个人都上台宣读评判文章。百货门市部的杨世珍紧紧张张结结巴巴地念他那篇文章,居然念成“王洪文在毛主席病重时,还在钓鱼打猪。”我搞了好半天才明白,中央材料的原话是“王洪文在毛主席病重时,还在钓鱼打猎。”这事让显周场上传诵了好几天。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清波讲话也好玩,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过去一个人做的事情,现在两个人就做了。”
【2】熊熊燃烧的墙架向我迎面砸下
那天黄昏时分,我们照例坐在诊所候诊室里开会学习,不知道是谁喊了一
声:“看,那边好像起火了!”大家急忙走出诊所往粮点上面望去,只见一股浓烟直往天上升腾,看样子好像是天井大队方向。于是立即休会,大家朝着浓烟的方向前去救火。
果然是天井七队发生了火灾,我们20分钟后就赶到了那里。那是一个大院子,全院都是木结构的老房子,着火即燃。烈火凌空飞腾,发出令人心悸的哔啵之声,火焰放射出的腾腾热气老远就滚烫灼人。现场一片混乱,伴随火光的是妇女儿童的号哭声,还有叫骂声。“谢新珍,你这个烂母狗,骚天刮地的烂母狗!”几个妇女都在咬牙切齿诅咒谢新珍。据说火灾是由于谢新珍煮饭不小心引起的。
在旁边的一块旱地里,一个头发散乱的女人揹着一个襁褓中的小孩伏在地上,头往地里撞,已经哭成了泪人。她就是谢新珍。
和我们一起赶到的陈德金书记站在院子外大声吼叫:“经常给你们讲,要防火,要防火,就是不听!”
火焰已经吞没了大半个院子,被燃烧后的木料通体透明,成为巨大的烧透的木炭,还一一保留着完整的形状。院子里还剩下小半没有接火,但已经岌岌可危。一些人慌着从自己家里抢东西出来,而没有考虑到先断火路,当他们还在抢那些并不值钱的东西时,烈火已经猛扑过来。
仍然有一些勇敢的人登上屋顶去断火路,火光映照出他们的伟岸身影。
想要用水灭火已经完全没有可能,经历过夏秋的连续干旱,田里已经没有一滴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粪池里的粪水打起来灭火。我平时从不豪言壮语,但是此时我毫不犹豫就抓起一只粪桶打粪灭火。在如同战场拼杀般的过程中,粪水一会就沾满了头发、脸面、衣裤,甚至溅到嘴里,臭不可闻。但是谁还顾这些。这时陈德金还在外面大声训话:“要把火灾消灭在隐患时期……”
火焰继续腾挪着,又一片房屋被火焰吞没了。一堵高高的墙架被烧得脱离了房屋主体,带着烈焰像一道牌坊似的横着砸下来,我正提着粪桶泼粪,看着墙架迎面向我砸来,赶紧往后退。只听见轰隆一声,那墙架倒在离我只有几尺的地方,跳起来的炭火溅到我身上。要是我动作迟缓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
救火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最终还是眼睁睁看着火焰吞噬了整个院子。只有最边缘的一间房子没有烧掉。那是年轻的杀猪匠杨显鹏的家。杨显鹏经常被食品门市部雇请来杀猪,我很熟悉。
供销社新来不久的副经理兼会计谢宝乾、毛烟技术员王兴龙等人在这次救火中也冲到最前面,全身都是火灰。
回到显周场,我从头到脚洗了个遍,换了衣裤,但即使如此,头发上的粪水气味还是几天都不干净,很恶心。
【3】我的皮鞋成了“忆苦思甜”的道具
运动初期一般都是平静的,慢慢就会有戏看了。
每次政治运动,“忆苦思甜”是百试不爽的法宝,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当然不能例外。不过,这次不像以前那样落套,采用了一些新的方式。举办忆苦思甜展览就是精彩一幕。
祝裕华是刚才结束了在新生区任家公社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后转战到显周公社的。在任家公社,他成功地揪出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萧伟。萧伟是任家供销社经理,曾经是全县的标兵,其先进事迹被《万县日报》大块文章报道,在供销系统长期传诵,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不知怎么回事,祝裕华很快就把萧伟搞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还把萧伟的罪行搞了一个全县巡回展览,萧伟一下就臭名昭著了。(1979年我调县土产公司,派驻任家搞青麻生产,与萧伟时有交往,得知已经撤销了对他的大部分结论,这是后话。)来到显周后,祝裕华把办展览的形式也带来了。这次办的是忆苦思甜展览。
忆苦思甜的永恒主题就是控诉地主的罪恶,述说共产党的恩情。根据这一主题,祝裕华在全公社大量搜集解放前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证据,比如找来量米的升斗——农村几乎家家都有,说成是地主大斗进小斗出的铁证,配上一段解说词:“地主的斗,吃人的口。倾不尽的血泪恨,装不完的阶级仇……”找来几件破烂不堪的衣服,说解放前贫下中农衣不蔽体牛马不如,穿的就是这样的破衣服——其实要找这种衣服太容易了,家家户户都是。找来几根木棒——那是地主毒打贫下中农的凶器……后来又找到了许多比较光鲜的衣裤,说是解放后贫下中农都穿上了好衣服,又找到了几只廉价的手表,说是贫下中农翻身做主如何如何。
祝裕华又抽调小学教师和插队知青组织了一支配合忆苦思甜展览的文艺宣传队,和我关系很好的黄天雪老师和鱼箭大队女知青高霞等人都是宣传队的主力。宣传队天天紧锣密鼓地排练“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什么的,很快就准备粉墨登场了。
展览筹备得差不多的时候,祝裕华忽然感觉还欠缺一点什么,为了表现贫下中农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最好还要有一双稍稍像样点的皮鞋。这就有点沮丧了,显周这个山沟,贫下中农虽然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大多是赤脚,即使穿鞋也是草鞋之类,去哪里找一双皮鞋呀。
祝裕华灵机一动,想到整个显周场上,可能只有陈仁德穿得时髦一点,他确实也注意到了我脚上那双亮闪闪的接尖皮鞋。这一天,祝裕华来到我门市部里,先聊了些业务方面的话,然后很委婉地说到忆苦思甜展览,讲了一大通“重大意义”,然后就把话挑明了,要我把鞋脱给他们拿去展览,表现贫下中农的“幸福”。
我从小就接受填鸭式政治教育,知道许多的“重大意义”,不过对祝裕华的要求还是有些出乎意外,稍稍犹豫了一下,很快就顺从地把皮鞋脱给了他。说实话,那皮鞋外面虽亮闪闪的,里面却是臭烘烘的,年轻人的汗重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几天后,忆苦思甜展览在完小一个宽大的教室里隆重开展,我随着人流走进展厅,一边唱着“天上布满星”,一边就看到了自己的那双皮鞋,居然被摆在很显眼的位置。靠近那双皮鞋的,是一双沾满泥土的烂草鞋,可能也是从哪位老农的脚上脱来的吧。在两双鞋下面是一张很大的纸,上面用浓墨写着,“请看,解放前贫下中农穿的是烂草鞋,解放后已经穿上了高级皮鞋。”我差点笑出声来……
忆苦思甜展览加上宣传队的现场文艺演出,引起了很大轰动,而且通过这次展览又培养出了几个觉悟很高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在现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潘经理爱流鼻涕的特点这次被发挥到极致,他一走进展览室就开始流泪,然后鼻涕大把大把喷涌而出,他也不用找地方涂抹了,就让鼻涕长长地挂着。
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潘经理从五十年代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前后20多年,写下的申请书足足有一尺多厚,可是不知何故,党组织却始终不批准。潘经理把这看成是党在考验他,一直不停地写。这次运动一开始他就向工作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真的是时来运转了,工作组已经密切关注他。此时他一边看展览,一边就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工作组的同志被感动了,要他在留言簿上留言,他提起笔来一口气写了满满一大页,字字血,声声泪,还伴着鼻涕,场面十分感人。这一下,工作队认为忆苦思甜展览非常成功,超过了他们的预想,潘经理作为典型,当天就写进简报传到县上。
“哦,原来这个同志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么深厚!”祝裕华说。
祝裕华一鼓作气,将展览转移到拔山区其他五个公社去巡回展览,均获成功。不久县里来了通知,说这样的展览很好,要安排到全县76个公社以及县属各系统去巡回展出,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于是,我那双幸运的皮鞋便随着巡回展览在“天上布满星”的歌声中走遍了全县城乡。记得那皮鞋是重庆南岸皮鞋厂生产的,购买于重庆三八商店,价13.78元。
巡回展览还没有结束,潘经理已经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的理想。
【4】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学大寨是那个年代农村永恒的主题。学大寨的口号不断花样翻新,诸如“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苦战三五年,普及大寨县。”“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领导。人家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了吧。”“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甚至延伸到了“教育也要学大寨”。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当然少不了学大寨。此时的学大寨除了造大寨田之外,还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好像资本主义随时都会复辟。其实中国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哪里谈得上复辟?绝大多数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连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见过,哪有资格高谈资本主义?
师联8队队长黄某忽然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揪出来了。其主要事实是,他居然购买了一个爆米花机器,带着小儿子走村串乡去帮人炒米米儿。公社书记陈德金得知后,在公社礼堂召开大会,把这个队长带到台子上来批判。那天我正好也参加了会。
队长上台时,把一个被烟火熏得黢黑的爆米花机器和一个高大的竹篓子也揹上台来做“反面教材”。他沉痛地批判自己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家致富,但是岁数大了,学手艺已经来不及,想来想去,只有炒米米儿最简单,不需要什么手艺。买个米米儿机,嘣的一下就是一角钱。我就喊我十多岁的儿子揹起竹篓,我挑起机器去转乡……钱是找了几个,称盐打油都有钱了,可是却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
他说的“嘣的一下”,是指的爆米花机器炒熟后打开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当时市价是每炒一次收费一角钱,所以说“嘣的一下就是一角钱”。
资本主义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就在我们身边,简言之,个人外出炒米米儿挣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家一起在队上种田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队长欢迎大家帮助他批判他,再也不敢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那段时间公社还真堵死了资本主义的路。一天,我惊讶地看到一群人押着一个少年从场上走过,陈德金书记走在最前面。那个少年只有十四五岁模样(后来得知是15岁),胸前却挂着一块很大的纸板牌子,上面写着“破坏农业学大寨”。我很纳闷,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怎么破坏农业学大寨?问一旁的人,才知道这个少年不愿意去修造大寨田,说:“老子不想去砌坎坎。”砌坎坎就是用石头修建大寨田的田埂。只听见陈德金一边走一边大声说:“我们要和反对农业学大寨的人作坚决的斗争”。这个少年从第二天开始,胸挂着牌子到12个大队去轮流游乡。这样的斗争效果很明显,一时再也没有人敢“破坏农业学大寨”了。
戏剧性的故事发生在几年后。陈德金书记为了让儿子顶替工作,被迫提前退休回到八德公社乡下。这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贫困的农村,爆发出发展生产的巨大活力,经营副业不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些能工巧匠成了最早的“万元户”。陈德金此时心里也痒痒的,想找生财之道,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再去学艺已经不可能。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师联8队队长黄某在被批判时说过的话:“岁数大了,学手艺已经来不及,想来想去,只有炒米米儿最简单,不需要什么手艺。”他顿时眼前一亮,茅塞顿开,立即买来爆米花机器,去花桥、八德等乡场赶集炒米米儿。这时,“嘣的一下就是一角钱”已经涨成了两角钱。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喜剧情节很快在忠县后乡流传,不久传到我耳中——那时我已经返城上班。我不禁拊掌大笑——几十年里反复批判资本主义,怎么到头来会是这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听说陈德金炒米米儿引起反响过大,对他造成压力,他被迫半途而废,卖掉爆米花机器回家种田——他可是个种田好手。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曾经在忠县城惊喜地邂逅陈德金,他已经七十多岁,穿着城里少有的蓝布衣服,牵着一个小孩——可能是他孙子。“陈书记……”我大声招呼他。可能他已经有多年没听见过这种称呼了,一时没反应过来。“陈书记……”我又大声叫他。他愣了一下,终于明白是在叫他,赶紧“嗯嗯嗯”的答应。我问:“陈书记,不认识我了?我是显周供销社陈仁德呀。”这下他想起了,很激动地和我握手。我感觉他满手都是粗硬的老茧。“老陈……你,现在已经在哪里上班?”居然还是几十年前的口头禅。我简述了这些年我的情况。陈德金连声说:“还是你好啊。”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