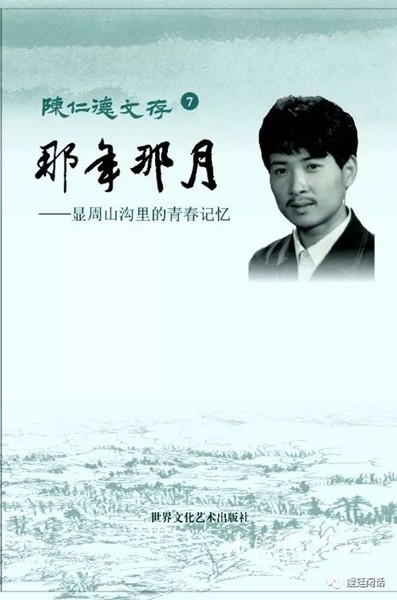
【4】来了个水灵灵的女知青
这一天,我照例开门营业,闲场天,没多少人,就坐在柜台里发呆。忽然我眼前一亮,走进来一个俏丽的姑娘。这姑娘十六七岁,水灵灵的丹凤眼,白皙的瓜子脸,乌黑的长辫子,细长的手指勾着一顶洁白的草帽,草帽上印着四个红字“上山下乡”。我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新来的重庆知青。
和这个姑娘一起走进来的还有一个老农民,是沥石一队的潘队长,我认识。潘队长是来为新知青购买农具的。
潘队长选定了一把沉甸甸的锄头,顺手递给那位姑娘,那姑娘双手接住掂了掂,面有难色,轻轻说了声:“这么重啊”。潘队长转身又选粪桶去了。
这个从重庆来的女知青叫刘永秀(后来我在作品中曾化名秦韵秀),插队沥石一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静秀美。大概刘永秀不大和公社其他知青交往,真是全身心在队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此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再见过她。
有一天,又是为了什么形势需要,公社搞了一场文艺汇演,各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到公社的破庙里依次登台表演。那时的文艺节目不外乎就是“四个老头学毛选”,“我参观大寨回家转”之类的,索然无味,我是绝不去看的。但是离得太近,声音总会飘到我耳朵来。“我们是公社的铁姑娘哎嗨哟,延河边上的女石匠……”闹嚷嚷硬邦邦,哪有一点美感。过了一会,歌声再次响起,却象银铃般的美:“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草原和北京紧相连……”一下就吸引住我。在这个山沟里,哪来这么好的声音呢?我马上关门,跑进公社去踮起脚跟看。哦,水灵灵的丹凤眼,乌黑的长辫子,只是白皙的瓜子脸略有些黑了……原来是她,刘永秀。她继续忘情地唱着:“骏马行千里,雄鹰飞蓝天。新牧民扬鞭高声唱,我爱祖国的大草原……”歌声激越清扬,如同在破庙里漾起一阵春风。
这便是刘永秀给我的第二印象。她是那么清纯甜美。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有些令人沮丧。
沥石一队有个叫潘宗堂(后来我在作品中曾化名樊中康)的大龄青年,快30岁了,还孤身一人找不到老婆。为什么呢,因为潘宗堂是个无父无母无亲无戚的孤儿,穷得叮当响,住在一个狭小的破草棚里,天穿地漏难避风雨,所有财产加起来可能不值十元钱。更让人避而远之的是,潘宗堂肮脏邋遢,满头疥疮——俗称癞子。这个家底加上这个形象,潘宗堂明白自己不会有人喜欢,已经认定一辈子打光棍了。
潘宗堂虽然条件很差,但是心眼不坏,劳力很好,他看到刘永秀一个大城市来的姑娘可怜兮兮的,就主动帮忙做点农活。他这样做绝非有什么动机,他哪敢。但是奇了怪了,刘永秀的芳心竟然被他打动了。刘永秀觉得,在这个穷山沟里,潘宗堂是唯一体贴帮助她的人,也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她竟然匪夷所思地爱上了潘宗堂。
潘宗堂被忽然从天而降的好事吓坏了,他不信这一切是真的,他祖宗八代也没修到这么好的命啊。他坚决拒绝了刘永秀。但是,刘永秀却很坚决,非要和他相好,甚至不惜以身相许。
事情发展到这里,凡是怜香惜玉的人,我想都会痛心疾首,但是,悲剧才仅仅开始……
【5】女知青跳楼殉情
很久不到显周赶场的刘永秀忽然频频出现在场上,她不是来参加知青聚会,也不是来取邮件,而是来办理结婚手续!潘宗堂和刘永秀一起走过显周场时,像做贼似的缩头缩脑,刘永秀却昂首挺胸,像在台上唱歌一样的从容。这让公社的干部们大吃一惊,让所有知青也大吃一惊。文静秀美声如银铃的刘永秀要和癞子潘宗堂结婚,有没有搞错?
公社拒绝为他们办理结婚证书,起初是说要“提倡晚婚”,后来又说知青到农村是接受再教育的,不能过早考虑结婚的事。反正就是不给办证。陈麻子书记还单独和刘永秀谈过话,要他“悬崖勒马”。这就是刘永秀频频出现的原因,公社不办,她就每次赶场都来闹着办,铁了心要结婚。
公社的全体知青都议论纷纷,认为刘永秀给知青丢尽了脸,刘永秀索性不再参加任何知青的活动。
这一天,刘永秀和潘宗堂最后一次到公社办结婚证,刘永秀说:“再不办,我们就自己宣布结婚,不要你那个结婚证,我们照样结婚。”公社当然还是不给办。刘永秀回到沥石一队后,自己选了个晴朗的日子,在院坝里燃放了两挂红红的鞭炮,一阵噼里啪啦响过后,就向乡亲们大声宣布:“我们今天结婚了!”随即把自己的床铺锅碗等搬到潘宗堂的草棚里,开始正式度蜜月。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奇特的婚礼了。一个大城市里的美女和一个穷山沟里的癞子,不要结婚证,不宴请宾客,免去所有繁文缛节,只需要两挂鞭炮和一个破烂的草棚。
消息迅速传回了重庆,刘永秀全家被惊呆了,立即写信给刘永秀,要她和潘宗堂断绝关系。可是,刘永秀根本不听,回信表示要和潘宗堂过一辈子。初冬的一天,刘永秀的父亲和哥哥从重庆赶到显周沥石一队,他们的突然出现,让刘永秀大吃一惊。潘宗堂见到岳父和舅子,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喊名字。刘永秀的父亲看到女儿住在一个破烂不堪的草棚里,女婿又是那副模样,比自己想象的还差,不禁鼻子发酸。刘永秀的哥哥则勃然大怒,气得两眼冒火,当下如同饿虎扑食般扑上去给潘宗堂一顿拳脚,刘永秀死死护住潘宗堂,但是哪里护得了,潘宗堂只有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刘兄还不解恨,索性将草棚里的盆盆罐罐一气砸得稀烂才罢休。
第二天,刘永秀被父兄强行挟持回了重庆。离开显周场时,我看见她被父兄一前一后夹在中间,从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走过。她头发散乱,眼睛红肿,眼中噙着泪花,头一直低着,穿一件那时比较时兴的蓝色短棉大衣,手往袖口里面缩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件事要是到此为止就好了,可是偏偏结束不了。谁也没有想到,10天后,刘永秀又出现在显周场上。我看到她在场上孤零零地徘徊了一阵。这次她再不是那个文静秀美的姑娘了。她失魂落魄,憔悴不堪,昔日水汪汪的大眼睛变得呆滞无神,充满忧伤,脸庞拉的老长老长,头发胡乱地扎在脑后,如同乱麻。有好心人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沉默不语,只是流泪。后来她终于开口说话,才知道了她这10天的情况。
原来,刘家父兄把她带回重庆后,全家包括三亲六戚都来开导她,劝她不要一时糊涂毁了一生前程,劝她以骨肉亲情为重,从长远着想,彻底断绝和潘宗堂的关系。家里正在找关系把她的户口转到重庆附近另外一个山区县插队落户,这是当时的知青政策允许的。只要户口转走了,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没有人会知道以前的事情。
家中亲人的苦口婆心也够感人了,道理也说得很透彻了,可是,刘永秀已经铁了心要跟潘宗堂一辈子,她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对所有劝告一律断然拒绝。家里没有办法,只好把她反锁在屋里,以为过一段时间总会慢慢醒悟。
谁也没有想到,刘永秀趁家人不备,偷偷跑出家门,竟然步行600里山路回到了显周。她身无分文,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挨饥受冻,吃尽了苦头。所以走到显周时已经是失魂落魄憔悴不堪。所有人听了她的故事都唏嘘不已,为之动容。
刘永秀当天回到沥石一队那间草棚里和潘宗堂抱头痛哭到深夜,决心重建家园,白头到老。乡亲们大为感动,一家送来一个碗,就是几十个。其他用具也凑了些,家又兴起来了。
几天后,刘家父兄气势汹汹地再次追到显周,在公社革委会配合下,再次将刘永秀挟持回重庆。可惜这次我有事外出,没有见到刘永秀临走时的场面,但可以想象那场面一定是极其悲凉的。
刘永秀这一去便没有再回到显周来,家里对她加强了防范。但是,不久就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刘永秀在确知无法回到显周与潘宗堂团圆后,勇敢地纵身跳下高楼殉情了。死时年仅19岁。
噩耗传到显周,乡亲们皆为之扼腕,有些老婆婆失声痛哭。潘宗堂却傻傻的,呆呆的,一言不发。
邻村天井八队双目失明八十老翁杨继业(与宋代杨老令公同名)听说此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拊膺长叹,慨然作歌曰:
前年秋风起兮你来时,
今年雪花飘兮你归去。
鸳鸯有意成双飞,
风雨无情故折翅。
吁嗟乎,永秀妹,
你今去,为何去?
长教人间添相思。
农村耕田我是一孤子,
城市读书你是一淑女。
只因柔意怜穷途,
遂把温情将我许。
吁嗟乎,永秀妹,
你今去,为何去?
江河有尾恨无际。
且将悲歌一曲寄相思,
料得多情人儿梦魂知。
今生未作并蒂莲,
来世愿为连理枝。
吁嗟乎,永秀妹,
你今去,为何去?
月照空房倍惨凄。
歌词酸楚,极一唱三叹之致,令人不忍卒读。
古之烈女,亦不过如此。然而归根到底,刘永秀终是时代悲剧。1998年,我在《三峡都市报》工作时参加万州区知青岁月征文大赛,以此题材写的《跳楼殉情的重庆知妹》荣获唯一的一等奖,我当时写有一首七绝:
敢从乱世证姻缘,倩女坠楼犹少年。
最是痴情人不解,空教侪辈至今怜。
此事我为何知之甚详,除了我自己就是目击者,还从显周小学教师邹道权那里了解了许多发生在沥石一队的事情。邹道全的妻子潘宗淑是沥石一队人,和潘宗堂同一个院子,那个生产队的人全都姓潘,故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情节。
【6】端午前夜顔光宗被砍成重伤
显周虽然是一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弹丸之地,但是却不断有惊人的故事发生,使得田边地角的老太太老爷爷们总是不乏谈资。1976年端午前夜,紧邻显周场的前进3队(现为双塘6队)又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前进3队队长叫颜光宗,约40岁,高高大大,头上包着白帕子,手里握着一个叶烟管,满面堆笑。因为离场很近,准确地讲,显周场的一部分就是属于前进3队,显周小学就在前进3队地盘上,所以,颜光宗和场上各单位的人都很熟识,早不看见晚看见。我们供销社的伯有训还经常和他开玩笑说怪话。
颜光宗的哥哥叫颜光祖,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两兄弟一个队长一个副书记,在队上当然就有些势力,一般人都敬而远之。
这队上有个社员叫颜平安(队上颜姓特多),约30多岁,是个木匠,因为做木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就搁着木工的斧头刨子没用,天天在家学大寨——做农活。颜平安可能生过什么病留下后遗症,神情略有些痴呆,面部表情有些僵,但是他老婆却生得不错,端端正正的。
颜光宗按家族里的辈分,应该是颜平安的大哥,可是却暗暗打起了平安老婆的主意。在他眼里平安整天傻傻的,好对付。他采用调虎离山之计,晚上派平安去值守公房,也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值守公房只需要晚上去公房睡觉,毫不费力就可以得工分,平安也很乐意。平安去公房睡觉后,颜光宗就去平安家偷情。平安的孩子还小,早早就睡了,颜光宗没有什么顾忌。平安的老婆起初当然是不干的,后来迫于队长的反复挑逗也就上床了。
颜光宗大概是尝到了甜头,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巴不得长期占有,就经常派平安去值守公房。这样一来,就难免露出马脚了。
首先是队上有了一些风言风语,然后平安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别说平安傻傻的,他对自己的老婆做没有做什么还挺明白,慢慢的他就拿定了主意要报复颜光宗。
1976年端午的前夜,也就是农历五月初四,颜光宗大概是想在节日里浪漫一下,又故伎重演,派平安去值守公房。平安二话没说,就往公房去了。颜光宗和平安的老婆都不知道,平安这个平常看起来傻乎乎的小子,去公房的半路就悄悄折回了家中,在床后的角落里潜伏着,这样一来,惊人的故事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了。
平安是木匠,有一把锋利无比的砍木头用的斧头——当地叫开山,此时他早已在床后手执利斧只等颜光宗到来。那时煤油紧张,为了节省,很多家庭晚上都不点灯,平安老婆为了偷情,当然更不会点灯。在黑暗中,一场血腥仇杀即将上演。
颜光宗和往常一样,进了屋就巴不得立即搂着平安老婆上床。说时迟那时快,正当颜光宗摸索着靠近床头时,黑暗中闪过一道寒光,利斧嚓的一声砍中了他的腰部,幸好是擦着砍过,伤口不深。颜光宗大惊失色,往前一倾,这时第二斧已经到了,他的屁股从上到下被劈开了一条七寸长的口子,血往外涌。这时平安已经叫出声来:“老子砍死你个狗日的!”颜光宗此时彻底明白了。他侧身往旁边一挪,赶紧往外跑。这时第三斧到了,他的腿部侧面被利斧划过。
“救命啊!”颜光宗顾不得面子也忘记了疼痛,大叫着往外跑。院子里的人看见他满身鲜血,都吓坏了。平安此时和程咬金一样,三板斧后,神力已去了大半,丢掉斧子不再追赶。
颜光宗10分钟后便被抬到了公社卫生所,这已经是夜半时分,所长丁明文医生立即起身做手术,清创、缝合,搞了几个小时。就创伤而言,这是丁明文医生做过的最大的手术。
第二天一大早,颜光宗偷情被砍三板斧的新闻迅速传遍显周场。那天是端午,按照惯例,山民们都要来赶场,一时场上人山人海拥挤不通。颜光宗住的病房正好窗口向着大街,那间病房成了当天显周场上万众瞩目的风景,无数人拥挤在窗前,争先恐后攀着窗口的木条往里看,还边看边议论:“就是他呀?”“砍得好!”“划不来哟。”从早到晚,蔚为壮观。颜光宗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默默地忍受着从窗外射进来的利剑般的目光。
我和伯有训直接进入了颜光宗的病房,伯有训披着一件旧蓝布制服,笑嘻嘻地俯身对颜光宗说:“你各自家里有个恹皮皮(指老婆),多擩几下就是噻。”真把颜光宗搞得哭笑不得。我们问丁明文医生,伤势到底如何?丁明文正握着一个约七寸长的烟杆在抽烟,他举起烟杆说:“最长的一个伤口,有这个长。”
从那以后,颜光宗再也不敢去平安家里偷情了,斧头还在那里搁着呢。平安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大家都认为他做得对,是条汉子。他老婆难堪了一阵,也和平安过起了平静的日子。
2013年7月23日,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我在拔山杨柳阿金河度假村见到一个开馆子的姓颜的小伙子。当得知他是显周前进大队人时,我便问他:“颜光宗还在吗?”那小伙子却反问我:“你说的是不是‘三开山’?”(当地把斧头叫“开山”),这让我大吃一惊。颜光宗偷情被砍时,这个小伙子还没有出世,他怎么脱口就说出“三开山”来?他见我狐疑,就说:“我们那里都知道颜光宗被砍三开山的事,大人小孩都叫他三开山。喊惯了,他也不当回事,还要答应呢……他已经死了多年。颜平安……也死了。”
【7】我如此坚持原则
我在经管生产门市的同时,还负责经管食品门市。食品门市两个人,一个人管开票收钱,一个人管杀猪卖肉,以前是韩家虎和李洪安搭档,韩家虎交给我了,就是我和李洪安搭档。李洪安是个老屠工,技术熟练,为人木讷,从不多言多语。杀猪之外,他什么都不会,也不管。他是花桥公社宝胜大队人,老婆叫萧应梅,育有三个儿女,都才几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供销社为职工家属子女办医疗证,要登记姓名,他连儿女的名字都记不得,说:“我反正是喊李二李三,没有喊过名字。”真有趣极了。
一般情况下,每场杀一头猪。场口食品门市外的石坝就是屠场,李洪安将猪放血后分割成左右两大块,分别称出肉、边油、蹄、腰、肝、心、舌、肠等的重量,将数量告诉我,我就按照总量开票发售,购肉者凭我开的票去案桌上找李洪安买肉。结束后我和李洪安对账,看总共卖出多少,我根据开出的票做成日报单上报拔山区供销社。
肉食是那时最为紧俏的消费品,许多人一年四季都吃不上一次肉。开肉票的人那时是最吃香的,为了吃肉,许多人被迫在开肉票的人面前低声下气,如同乞讨般哀求开一点肉。我掌握了开肉票的大权,却不会弄权,始终坚持什么原则,坚决不开后门。现在想起,真傻得可以。
公社分管供销社工作的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清波,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潘经理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腰都不敢伸一下。按理说,我也应该和刘清波主任搞好关系,不能顶撞他。
这天,刘清波一反常态,非常客气地来到我屋里,说些不着边际的套话。我估计他肯定是有事相求,不然不会如此。刘清波的话慢慢变得结巴起来,可能是在考虑如何措辞更恰当。过了一会,他果然吞吞吐吐地说:“老陈,我想买两斤肉……我女儿最近要订婚……”看得出他说话的口气有些自卑。
要是换了别人,肯定马上就照办了,可是我不。我对刘清波主任说:“你经常讲,不能开后门,不要搞特权。没有肉票是不能买肉的,这你知道。”
刘清波的脸色非常尴尬,他没有多说就很狼狈地转身走了。
一会儿,潘经理来找我了。他叉着手弯下腰轻言细语地说:“老陈,还是给刘主任开两斤肉吧。他女儿订婚。”
我以同样的方式把潘经理也顶了回去,他很没趣地走了。
又过了一阵,刘清波拿着两斤肉票来了,是潘经理给他的。票证都是潘经理自己油印的,全部由他负责发放。我无话可说,乖乖地给刘清波开了两斤肉。
当时,我认为我做得很正确,坚持原则嘛。上级不是天天喊不准开后门吗。没想到我的所谓坚持原则就这样被他们轻松地戏耍了一下。想想刘清波主任也够可怜了,女儿订婚这样的大事,为了买两斤肉不得不放下架子来给我说好话,还碰了钉子。而我也太不近人情,近乎混账,完全不理解一个父亲的心情,还自以为是在坚持原则。
这种辛酸的事情,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发生,现在回忆起,已经恍如隔世。
【8】知青要把老人重做过
春节前,食品门市照例要出现杀猪高潮,这是为春节供应做准备。大量的肥猪被宰杀后制成盐肉堆积起来。盐肉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的发明,分割成左右两大块的猪肉被平铺在地上,撒上厚厚一层盐,像雪花一样,再铺一层肉,再撒一层盐,一直堆到屋顶。到了春节供应时,盐已经渗透到肉中,肉的颜色变得发黑,硬硬的,已经没有一点儿鲜味,难以烹饪,但好歹是肉,还是珍贵无比。春节前后很长时间,食品组基本上不再杀猪,一律供应盐肉,直到把库存盐肉卖完。
有些不适合制作成盐肉的副产品,比如猪血、猪肠、腰、肝、心、舌等就在宰杀后出售。猪血好像是每头猪0.10元,肠每斤单价0.28元,腰、肝、心、舌一律0.40元,现在想起真是太便宜了。
杀猪的屠场就在场口,食品门市旁边,石坝上到处是猪粪便,猪污血,还有混杂其中的枯草,腥秽不堪。杀猪时,等着接血的人提着木桶守在一旁,见到一头猪喷血而死,热腾腾的猪血流入杀猪磴下面的木盆时,便蜂拥上去抢,每次只能有一人得到,其余又耐心等。有一次,一个小伙子连续几次都被人家抢先抓到了木盆,他气不过,当众脱下裤子对着血盆撒了一泡尿,尿水混进猪血里,大家都别想。
我开票的窗口就在食品门市小屋里,窗外就是屠场。每天无数人排成队来开票买肉。前面讲过,每年春节要给农民每人供应半斤猪肉。窗口约两尺见方,被拥挤的脑袋塞满了,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后面长长的队伍。大多数人还是讲规矩排队的,但是只要有少数人一挤,队形就乱了,往往这时就骂声一片,难分难解。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一个年约七十的老农民排了好久的队,已经靠近窗口了,这时中苏大队(现在好像叫三坪村)一个姓张的重庆知青忽然从斜刺里挤进来,把老农民挤出老远。老农民气坏了,大骂这个知青不讲理。姓张的知青也用刚学会不久的本地粗话对骂,骂到最后竟然大叫:“老子把你重做过!”这下那个老农民肚子都气爆了,差点说不出话,好像受了奇耻大辱,愣了一阵才张口结舌地说:“老子七十岁了,你一个嫩苔苔,要把老子重做过?”张回过头去又说了一遍:“老子把你重做过!”那老农民不再答话,转身去屠场里抓起一根吆猪的响篙(竹竿),在满地的污秽中搅起一大团发臭的稀烂的枯草来,沾满猪粪和烂泥,高举着向张冲来,所过之处,污秽像雨点一样乱滴。窗口前的人一下散开,生怕污秽滴到身上。这时张已经从我手里开到了肉票,也急忙跳到一边。污秽擦着他的衣服滴下。老农民怒喝:“你个狗日嫩苔苔,你要把老子重做过……”
张可能不知道那句话的分量,很流畅地又说了一遍,然后拿着肉票跑远了。
那个张姓知青平时很文雅的样子,是重庆标准件厂的子弟,其父母是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从上海内迁到重庆的。张应该是上海人,在那个年代,可以十分从容的运用山民们的脏话去辱骂一个无辜的七十岁的老农民,恶劣到如此程度,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可见知识青年到底在农村接受了些什么“再教育”。
我一人身兼两个门市部的确很累,忙不过来,几个月后,我坚持把食品门市部交还给了韩家虎,少去了许多麻烦。
【9】公社厕所景观
一些制作竹器木器鞭炮的手艺人先后来和我拉关系,希望我收购他们的产品。一次,长岭公社一个织撮箕的人挑着他的产品来到我门市。我看了,他的产品质量很好,但是我撮箕库存充足,暂时不缺,就没打算收购。
此时正好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我的一大串钥匙不小心掉到公社厕所粪池里了,正束手无策。
这位不知名的手艺人得知后,在我并没有请他帮忙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就主动跳进粪池里去为我打捞钥匙。粪池里的粪水过膝,蚊蝇成阵,蛆虫如山,他俯身双手在粪池底摸索,赤膊上一会就叮满了蚊蝇,他双手皆是粪便,也不能去身上拍打,只好任凭蚊蝇死死盯着。他在粪池里很大的范围内反复摸索都一无所获,只好失望地“上岸”了。为了到小学那边的小溪去洗涤,他一直满身是粪走过全场,那些蚊蝇已经叮到肉里了,挥都挥不开,一直叮着他走。
钥匙最终没有找到,但是我已经很感动,把那批撮箕全部收下了。我找场上做“冷桌”(小型钳工修理)的师傅来重新配了钥匙。
关于厕所,实在不想多说,因为太肮脏,但是厕所却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所以,我只有忍着恶心再写几段。
显周公社厕所在诊所的旁边,是显周场上惟一的公共厕所。厕所大约有十多个平米,中间用竹壁隔成男女厕所。农民们那时绝没有使用手纸的习惯,都是用竹片,方便完了,顺手就在中间的竹壁上去折一块来使用。,久而久之,男女厕所互相洞开,如厕时尴尬之极。而一些人并不尴尬,居然可以轻松地和隔壁女厕所的人谈话。一些人不管厕所多么肮脏,还可以一边蹲下大便,一边吃东西。
大约从1975年开始,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开始了。县上组织的宣讲队来到显周大讲特讲计划生育。一个年仅22岁的小伙子在宣讲时现身说法,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一时,手术队游走在各个院坝,就在院坝里做男性结扎术。男人们像牲口被阉割一样,经过简单的消毒就手术。由于医务人员都是简单培训后上岗,技术很成问题,加之院坝手术缺少设施,许多人术后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有的甚至丧失劳动力。
何正虎就是此时做的结扎术,他的年龄大概30出头,给他做手术的是拔山区医院的周医生。周医生比较有名,不像那些在院坝里草率手术的人。在显周诊所的手术台上,我看见周医生将一个火柴棍大小的钎子穿过刚切下的约一寸长的输精管,举示在场者,证明手术成功。
公社诊所里经常住进一些被强制引产的妇女,引出的胎儿一律扔进厕所粪池里,很多胎儿都已经成形,在池子里重重叠叠堆积着,如厕时通过便孔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些胎儿在粪池里渐渐地被蛆虫爬满,直到完全被吞噬,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我每天如厕,总要面对这一惨景。
街上一个姓余的老农在离粪池不远的地里种了一畦烟叶,他专门用公社粪池里的粪水,实则为胎儿的尸水给烟叶施肥,那年他的烟叶长得特别茂盛。茂盛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人们说,那畦地的烟谁敢吃啊!
【10】宏伟的黄钦水库
修水库一直是人民公社化以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忠县最大的水库是黄钦水库,因位于黄钦公社而得名。黄钦水库开工于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据说建成后可以灌溉马灌、拔山、新立三个区的13个公社,其引水干渠分东西两条,总长度58余公里,跨越三区。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黄钦水库就开工了,我到显周公社工作时,黄钦水库还没有修好。修建水库的民工已经整整两代人。每年冬天照例要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民工们揹着撮箕,扛着扁担站在大坝上高喊口号。他们全部是无偿服役,自己带着工具和蔬菜,在工地周围搭建工棚或者借民房居住,除了补助粮食外,没有一分钱报酬,只是回到自己生产队去记工分。
显周场是新立等公社民工去黄钦水库的必经之路,每年冬天,一大早就有络绎不绝的民工扛着工具揹着粮草路过。从显周去黄钦水库约40里山路,漫长的道路上,无处不是前往工地的民工。我的门市里常常有路过的民工驻足停留,他们一个个面有菜色,衣衫不整,沉默寡言。
除了大坝工地,黄钦水库的干渠也是其延续的工地。经过显周的干渠至少十多里长,全部用长四尺高宽各一尺的石条筑成。由于是在山区,干渠要穿过很多山岭,飞跃很多山谷,于是就有了许多隧洞和渡槽。每天都能够看见在干渠工地挥汗大干的民工,他们舞动大锤开山取石,把坚硬的石头打制成一个个规范的条石,整整齐齐砌起来。大段大段的渠道已经逐步形成,那些飞跃山谷的渡槽尤为壮观,一排排的圆拱宛如一连串彩虹托起长长的渡槽,是绝对的好风景。想象着黄钦水库有朝一日开闸放水,哗哗哗的流水顺着数十里长的干渠,流过座座渡槽,流过道道隧洞,流进三区的田野,对于十年九旱的山区人民,该是多么激动人心。
我认识的许多农民兄弟和知青朋友,都去修过黄钦水库,他们为我描述大坝上的宏伟场面。大坝分为一坝和二坝,一坝高25.8米,长198米,二坝高22.9 米,长286米。仅在大坝上碾压夯土的大石磙就有几十个,每个大石磙高1.4米宽1.8米,用中型拖拉机拉着来回碾压。挑土的民工首尾相连望不到边,近处已经无土可取,要到七华里外才能取土。每个民工每天只能挑七担土,往返行程98里。宽阔的水库工地上有着近三万民工挑着担子来来往往,仅每天在狭路上被扁担碰伤的就有上百起。工地上,商店、诊所、邮政所、广播站、指挥部一应俱全,像个小镇。
那是粮食紧张的年代,许多民工是冲着吃粮去的。每个队都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开饭时,为了检验炊事员是否先偷吃了,有的人甚至要检验米饭中的“气眼”。“气眼”是蒸饭时为了透气用筷子在饭子中插的眼,一旦动过饭,“气眼”就没有了。
从开始修建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当年的许多民工已经死去,小孩也变成了老头,但是黄钦水库的水直到今天都没有流到三区的13个公社来。那些耗尽血汗建造的干渠,已经大段大段毁掉了,上好的石料被农民就近搬去修猪圈。只有那些宏伟的渡槽还高高屹立着,像古罗马残留的竞技场一样。早年那些白色的石头经过岁月风霜的侵蚀,已经变成黑色。渡槽里的过水明槽完好无损,只是,除了偶尔天上下雨外,从来都是干涸的。
据资料,三区13公社共无偿投工7000万馀工日,耗费粮食数十万吨,死伤残数百人。如果把所有民工的劳动折算成工价,更是一笔天文数字。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没有任何企业可以支付起这样的工价。如果某个企业像这样投资建设,再大的资产也早就破产了。当时要是把那些钱财用在改善民生上该多好啊。在那个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代,全国不知道有多少这样劳民伤财的工程。辉煌的是那些官员们当年“战天斗地”的功劳簿,悲惨的是那些流血流汗的一代又一代的民工。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