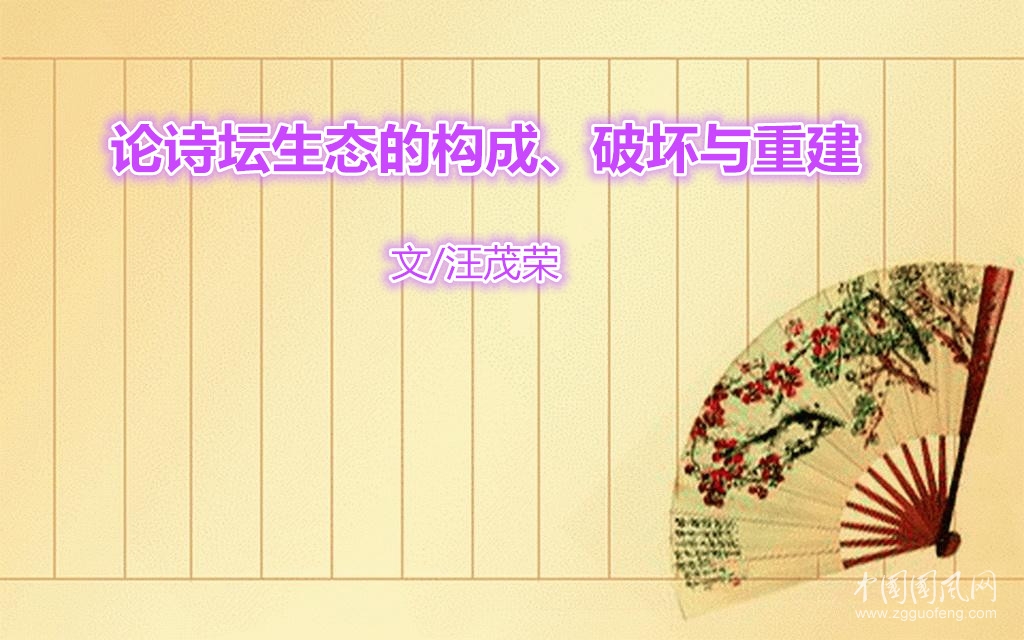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应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如从《诗经》时代算起,它起码已有着三千年的发展史。在这三千年的发展史中,曾涌现出大量的诗人,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作品,称中国为诗之国,应是实至名归,举世皆无间言的。正如自然界的动植物生存必须有相应的生态系统一样,中国古典诗歌取得如此繁荣的局面,也是与自身所拥有的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息息相关的。有了这个生态系统,古典诗歌便有了维系其生命所必要的土壤、空气、营养,而得到正常的发育滋长。降至近代,随着这个生态系统的渐次瓦解,古典诗歌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化,并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趋向枯萎。时至今日,要使古典诗歌重现往日的繁荣,除各种枝节性的努力外,最根本性的当是重建诗坛的生态。通过重建诗坛生态,为古典诗歌的存亡绝续、焕发生机,提供一个健全有效的良性机制。以下,即从两个层面,对这一诗坛生态的构成、破坏及重建,作一系统的探讨、分析。
诗坛雅俗互动机制的构成、破坏及重建
中国古典诗歌从广义上来说,应包括雅俗两大系。属于雅文学的,如楚辞、五七言古近体诗;属于俗文学的,如词(主要指早期的)、曲、谣谚等。诗史上这相异的雅俗两系不独“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且彼此取长补短、同荣互惠,构成了一个既自足又开放,具有良好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对于这一点,近人是颇有些清醒认识的:
中国文艺发展史告诉我们,历次文学创作的高潮都和民间文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楚辞同国风,建安文学同两汉乐府,唐代诗歌同六朝歌谣,元代杂剧同五代以来的词曲,明清小说同两宋以来的说唱,都存在这种关系。(郭沫若、周扬《红旗歌谣·编者的话》)
这段话讲清了民间文学即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影响,但受时代因素的制约,于雅文学对俗文学的影响却回避不提。这是很偏颇的。事实上,两者之间是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俗文学可以源源不断地给雅文学提供最基本的养料,从语言、素材、体制、审美取向皆是如此。正如前面所引用的,楚辞、建安文学、唐代诗歌等雅文学,均是在吸收俗文学养料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立足于俗文学这块土壤,雅文学就会失去必要的养料,与时代脱节,与读者分离,而日渐僵化、教条,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在一个民族文学的生态中,俗文学代表的是这个民族文学的广度,有了这个广度作依托,雅文学才能继长增高,日臻于完善成熟。韩退之所说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俗文学在体制上毕竟是原始的、粗糙的,在审美意味上也是贫薄的、伧俗的。它必须以雅文学作参照,下一番去粗取精的提炼工夫,其内在的光精才能得到集中的表现而大放异彩。没有雅文学作标准,缺少必要的雅化功夫,俗文学就会堕落为庸俗,甚至是低俗。而有了这一层雅化功夫,俗文学就会提升为通俗、雅俗共赏。通俗、雅俗共赏才是俗文学正常、健康的形态。文学史上《诗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都是由民间文学经过雅化,而变成雅俗共赏的通俗文学的典范的。如扩大范围来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如未经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这些文人的雅化,而仍只以宋元以来说唱形式流传,那它还算名著吗?还能赢得那么多读者吗?《刘三姐》中的民歌如未经音乐家雷振邦的加工,而只以原生态的形式演唱,那它还能拥有那么多的听众吗?很显然,其读者和听众的比例会大大减少的。在一个民族的文学生态中,雅文学代表的是这个民族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具有贵族性和精英性的特质。一个民族文学的最高规范是由雅文学来界定的,最深醇的品位是由雅文学来提升的,最大的权威是通过雅文学来确立的。只有在雅文学中,才能诞生这个民族最伟大的作家和最经典的作品。由这些可见,雅俗之间各有攸长,互为前提,形成了一个既互动又各得其所的良性文学生态系统。这个良性的文学生态系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长期存在着的。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但专制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却相对温和,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价值取向上大而化之的“定于一尊”,而很少落实到政策层面,对官方视野之外的文化形态采取铁腕手段予以打击、加以取缔。事实上,它是允许一个多元的文化生态系统存在着的。这个多元的文化系统的存在,确保了中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健康发展。只是到了近代,这一切才开始发生变化。
最先给这个文学生态系统进行打击的,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既曰革命,则所革的对象当然是前此占文坛主流地位的雅文学,尤其是其中的诗文二类。为此,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八不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钱玄同干脆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出于一种非学术性的考虑,在并无坚实学理的基础上,给雅文学贴上标签、罗织罪状,锋芒所及,雅文学生存的合理性被抽空,雅文学构成的基本原素被解构,雅文学与俗文学并存的多元性被取消。而这种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则直接破坏了雅俗文学良性互动的文坛生态,不是将俗文学雅化,而是将雅文学俗化了,并最终导致俗文学的一体独大和雅文学的被边缘化。
继之给这个文坛生态进行致命一击的是毛氏的《讲话》。在这篇影响历史的讲话里,毛空前强调了文学的工具性,视文学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因之文学要服从于政治,而“这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为了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就要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也就是,在立场上要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态度上要以歌颂人民大众为主,在工作对象上要服务于工农兵及干部,在工作问题上要做到“大众化”,在学习问题上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主义。凡与此五种价值异趋的,统以各种理由加以排斥甚至是否定。显而易见,他要肯定的是工具性很强的且已大大缩小了范围的俗文学,而遭到否定的只能是超越庸俗功利主义、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雅文学。在这里,毛氏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析法,将雅文学和俗文学完全置于一种对立地位,且不惜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在动机上是狭隘的,在方法上是机械的,在情感上是民粹的,在态度上是粗暴的。其直接的结果,是从内容到形式全面瓦解了雅文学。尤其是鼎革以后,这种带有极强政治功利主义的文艺思想迅速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在体制力量的推动下,更是所向披靡,无孔不入。经此致命一击,健全的文坛生态被彻底破坏了。
在健全的文坛生态破坏后,继起呈现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新景象呢?我们不妨将范围缩小到诗词界,再进行一番较为细密的考察。
首先是雅文学阵营发生了极大的分化。极少一部分立志不随流俗转的诗词家仍自占地步,按雅的标准进行写作。这些人从通都大市到穷乡僻壤都有,代表人物如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中国社科院的钱钟书,上海文史馆的潘伯鹰,安徽文史馆的刘凤梧。从这些人的诗集里,是找不出一首趋时之作的。也正是这些人,在庸俗的功利主义甚嚣尘上、审美普遍被政治势力绑架的时代,顽强地保存着诗词创作的高品位,黙黙传承着雅文学的一脉薪火。而这种固守也使他们付出了“负俗”的代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作为卓有成就的诗词家身份是不广为世人所知的,尽管他们自己视这种代价的付出为蔑如也。在吴学昭著的《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曾谈到七十年代钱钟书等人在其所住的陋室里从事《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的一段往事:
这项工作是1969年开始的,中断多年后于1974年11月又继续作。由于钱钟书“足不出户”,翻译小组的知名人士叶君健、袁水拍,不得不屈尊天天来陋室工作。叶君健与钟书脚对脚对坐,袁水拍挤坐一侧。周珏良代表乔冠华也来过几次。江青对袁水拍、叶君健说:“钱钟书不懂诗,你们让赵朴初去点拨点拨。”于是赵朴初奉命而来陋室,对“不懂诗”的钱钟书“点拨”,无椅可坐,只能挤坐钟书椅旁的凳上。钱钟书不声不响,听任他“听拨”。
此事杨绛在所著《我们仨》中也提过,可见印象的深刻和滑稽。钱钟书岂“不懂诗”?又岂是赵朴初所能“点拨点拨”得了的?尽管如此,却很能由这个事例见出彼时雅文学的命运。在那样的文坛语境中,像钱钟书这样的诗词界精英人物及典雅作品已不受重视,而逐渐被淡忘乃至消失在历史记忆的深处了,文坛重视的是赵朴初式的应时作品。不然,江青再无知,也不至于说钱钟书“不懂诗”;赵朴初即便“奉命”,也断不肯去“点拨点拨”钱钟书的。这是形势比人强,钱钟书虽不肯放弃自己的固守,也只好韬光养晦,“不声不响”,“听任他‘点拨’”了。
更大一部分诗词精英则放低身段,适时向“俗化”转型,不失虔诚地迅速融入新的诗词语境,并很快学会了用流行的语汇歌颂新的事物,在在张扬一种虚幻的幸福感。在这些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中,诗词的审美功能让位于诗词的宣传功能,诗词的政治性取代了诗词的人文性。缺少审美价值和人文精神,那还算得上堪称是雅文学精粹的诗词艺术吗?我们看在民国时期即已闻名于世的诗词家,如沈尹黙、唐玉虬、冒孝鲁等人在鼎革前后的诗作,以水准论,可说一落千丈,不啻出自两手。这里再以陈叔通为例。陈身历三朝,是公认的社会名流,有家学,中过进士,点过翰林,于国学有精深的造诣。本来是能写一手典雅的诗词的,而鼎革以后,却诗风丕变。如下面的两首:
太平天国有传薪,推倒王朝建在民。
革命开端功未竟,辉煌历史纪元新。
不忘前事有今朝,纪念从隆意义饶。
时代岂能无限制,破资立社导新潮。
诗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而作。原共四首,发表作196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上,这里选出的是其中的两首。从如此粗直的诗中,我们岂能看出陈的学养?这与老干体又有什么区别?曾有诗词行家对陈所作此类寡乎其味的大白话诗不以为然,拿给郭沫若看,哪知郭非常欣赏,认为变得好。(此项内容为余十多年前在某刊物所见,刊名及刊期待查)这表明陈叔通式的创作转型,已得到主流诗词家的认可甚至是鼓励。为此他们亦乐此不疲,尽管这是在将自己由诗词精英一步一步地变为诗词庸人。
雅文学阵营的分化在取径上虽有自我边缘化和主动转型的不同,但后果却是一样的。这就是诗坛精英阶层的整体“陆沉”,旧的诗坛权威及旧的标高也随之在公众视野里消失。而就在这“推陈”的过程中,适应时代的需要,诗坛新的权威借助超艺术的力量,也随之制造出来了。
绝对的权威当然是毛。毛氏于诗重三李,但似更欣赏“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他的为数不多的作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鼎革后的诗坛上大放异彩。尤其是经过体制内挂头牌的诗论家郭沫若的极富夸饰的阐释、推崇,更是成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我也敢于说,毛泽东同志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近年来正式发表了十九首诗词,更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郭沫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红旗跃过汀江”》)
毛之外,在当时有限的媒体上,经常谈诗、论诗、发表诗作的还有陈毅、郭沫若、赵朴初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几位诗人代表了诗词创作的最高水平,是新一代诗词界的权威。那么这些权威的真实水平又如何呢?毛的少数诗确有奇情,有壮采,诗中也有我在,具有如鲁迅所评的“山大王”气概。但整体来说诗功并不深,技术亦多有懈可击之处,一些未公开发表的诗更是大失水准。联系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及给这个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其中一些曾使人不寒而栗的诗,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吗?这样的诗只能聊备一格,是算不上权威之作的。即使在那种政治高压之下,一些诗坛精英对此种作品仍有清醒的认识,且不乏“腹诽”之作。近日拜读蕉窗老人刘凤梧先生的《蕉雨轩诗抄》,于系年1968年的《杂感》三首中有这样一首:
晚清词坛数彊村,壮采奇情继大樽。
我学倚声循制谱,人亡度曲剩啼痕。
瓣香堪挹红绒句,巵酒难招白石魂。
此调不弹逾廿载,是谁布鼓过雷门?
此诗为老人论词之作。如果我推测得不错的话,诗的尾联似是针对毛氏诗词而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时期,广播喇叭里经常播送的都是毛氏那些充满火药味的诗词。其时困居山村的老人正卧病在床,盈耳都是这样的声音,不能不使在诗词方面有极深造诣的老人产生“布鼓过雷门”之感。这固反映了老人的自负,也可见出毛氏之作是入不了真正诗词精英的法眼的。毛氏之外,陈毅将军文采风流,然亦只有诗情,诗学、诗功均浅,有些作品连格律也未过关,可以略而不论。郭氏有才学,懂诗,但于诗词创作只算是半路出家,功力并不深,兼之自觉地充当“党的喇叭”,一路跟风追逐,出手太易,由此而“逢场作戏”大批量生产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诚如他所自嘲的“诗多好的少”,只制造了无数的诗坛笑料,价值云乎哉!赵公出身名门,有家学渊源,本人亦极有学养,可惜为时势蛊惑而迷于抉择,在诗词创作上放弃了向上一路,而选择走了向下一路。他生前虽诗名极著,但所作充其量只是比较高级的宣传品而已,从长远来看,艺术价值并不大,就这一点来说,他与郭氏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些通过非艺术因素制造出来的诗词精英如按传统的标准来要求,是不足以代表雅文学,更算不上是真正权威的。从本质上来说,其所代表的仍属俗文学的范畴。但在旧的诗词精英群体分化“陆沉”后,这些准精英、准权威便抢占了原属雅文学领地的诗坛生态的制高点,并同真正的民间俗文学重新发生了关系。在诗坛新的生态系统中,并没有像旧的诗坛生态那样,形成雅俗之间的良性互动,各得其所,两全其美;而是以俗对俗,质言之是以高级的俗对低级的俗,恶性互动,终至两败俱伤。在这种恶性互动中,处于制高点一端的准精英人物,无意于且亦无能力对另一端的俗文学起雅化、提升作用,相反却为俗文学的进一步俗化呐喊助威,不至庸俗、恶俗不止。如:
1958年3月,“大跃进”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成都开会酝酿讨论。会上,谈到诗歌的创作,毛泽东表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写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民歌。”
(王振松《农民诗人王老九与郭沫若赛诗》,见《名人传记》2013年上半月第5期)
响应这个号召,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写文章给予理论支持,并作“采风大军总动员”,向全国各地发出搜集民歌的通知,“新民歌运动”随即兴起。郭沫若、周扬又合编《红旗歌谣》推其波而助其澜。在这种情况下,王老九式的农民诗人迅速走红,以至出现了“乡乡要出一个王老九,县县要出一个郭沫若”的提法,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文革,一些农民诗人甚至登上了大学的讲台,如安徽肥东县的农民女诗人殷光兰即登上了安徽大学的讲台。那么这些“新民歌”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且来欣赏其中的两首名作:
梦中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做活想起毛主席,周身上下增力气。
走路想起毛主席,手推小车不知累。吃饭想起毛主席,蒸馍拌汤添香味……
(王老九《想起毛主席》)
敢想敢说又敢干,好比三颗原子弹。炸开千年迷信锁,粉碎万年自卑感。
(《红旗歌谣·三颗原子弹》)
本来,民间文学是一座富矿,具有很多朴素的、优美的正面元素。而这些正面元素,是要有雅文学的眼光,才能发现、鉴别、引导而进入审美领域的。可惜此时诗坛生态顶端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雅文学的眼光,兼之别有所图,从民间文学中被刻意发掘出来的多是负面的如上所引的那些谄媚与噍杀兼而有之的乱世之音。这种乱世之音反过来又被曲解为“人民性”、“斗争性”、“通俗性”而为所谓的诗坛精英所肯定并吸收,因此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也频频出现了诸如“不须放屁”、“万岁高呼三脱帽”、“‘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等粗俗不堪的诗句。这种上下之间的恶性互动绑架了诗坛的审美,形成一种群众性文化暴力,并在文革时期被推向极致。而它留给当代诗坛的一个颇为尴尬的遗产,则是“老干体”这个庞大的存在。
“老干体”,按传统的诗坛架构来说,既不属于真正的雅文学,也不属于真正的俗文学。它横亘在雅俗之间,虽略具二者的皮毛却又两头都够不着。向上,它够不上雅文学的标准,也不愿走下学上达一路;向下,它没有俗文学的质朴和生气。对自己的生存它深感迷茫,缺乏理想,只在诗坛平庸地混日子。如果还有出路的话,那它认定的最好出路就是在改革的名目下,将平水韵解构掉,将格律解构掉,将纯粹典雅的文言解构掉,直到把诗词这种雅文学的基本要素统统解构掉。如果真走到这一步,那还能算是代表雅文学最高成就的诗词艺术吗?很显然,按“老干体”这种不断降低标准的思路,诗词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之路是走不通的。
在较为细密地考察了诗坛雅俗良性互动机制的构成及解体的历程后,正面的意见实际上也已包含在其中了,这就是要确保当代诗词的健康发展,就必须重新激活诗坛雅俗良性互动机制。
其一,要重新摆正雅俗之间的关系。走向上一路,让雅引领俗;而不能走向下一路,让俗引领雅。这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不坚持这个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诗坛良性的生态是建立不起来的。尤其是在这个俗普遍侵蚀雅、整个民族文化水准空前跌落的时代,此点更为重要。
其二,要重新认定艺术的标准。艺术的标准通常是由权威来代表着的,所以要承认权威,要尊重权威,要确立权威的权威地位。也许有人以为当今是一个张扬个性、不要权威的时代,再没必要这样提权威问题。其说虽辩,而实是一种误解。个性有艺术个性与自然个性之分。自然个性是权界意义上的,权界意义上的个性是不承认有权威的,它允许每个人都性其所性,进行自由的发展;绝不扬此抑彼、以权威的名义去侵犯另一个个性的发展。艺术的个性则是审美的,审美意义上的个性是承认有权威的;权威就是一种比较特出的艺术个性,尊重权威就是尊重高品位的艺术个性。如果对这种高品位的艺术个性都没有眼光来欣赏和尊重,又怎能自觉地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即便是挑战权威,也要以尊重权威为前提,挑战与尊重并不是矛盾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动辄就要解构的痞子文人式的做派,不是尊重个性,而是在张扬另一种意义上的奴性。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曾说过两句发人深省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两句话同样也适合诗词界。尤其是在传统诗词存亡绝续的非常时期,就更是如此。而真正的权威一旦得到了承认和尊重,那些伪权威才相形见绌、失去生存的空间,诗坛真正的标高才能确立,对俗文学的提升和引领才会有可靠的尺度,诗坛雅俗良性互动机制的激活也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其三,要重视俗文学的基层性。要源源不断地从俗文学的基层性中吸收正面的资源和获取负面的参照,正面资源有技术上的,但目下主要还是素材上的。俗文学(此处主要是指层次尚低的诗词创作)面广人多作品量大,有着素材上的优势,诗坛精英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否则,一味端坐书斋,专作“瞎唐体”,是要与时代脱离的。负面的参照是指时刻关注俗文学走向,及时把握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将对俗文学的引领、微调、雅化落到实处。由前者,可以使雅文学做到雅而不空;由后者,可以使俗文学俗而不恶,保持大俗大雅的品质。雅俗之间只有保持这样的互动,才能将良性的诗坛生态彻底激活。
培育诗人的人文机制的构成、破坏与重建
在传统的诗坛生态中,诗人的成长不是一种孤立的纯个体行为,而是有一整套人文机制在起着有效的培育作用的。这套人文机制通常由家学、师承、交游三个板块组成。就每个个体而言,尽管并不绝对兼备,作用程度也会有所差异,但大致还是能概括古今一切诗人的成长历程的。
家学对于一个诗人的成长来说具有原初的意义。它一般是通过生物意义上的基因遗传和人文意义上的基因遗传作用于每个诗人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遗传赋予诗人以特殊的天分、独特的气质,这些都是先天的,此处可略而不论。人文意义的基因遗传往往表现为带有家族特征的精神资源的积累,教育范式的建构,学术路数的确立,审美风格的认同。诗人若从小就沉浸在这种家族文化环境里,便会受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内化为一种宛若天成的人文秉赋。家学所打上的这种最初的精神底色和提供的丰厚凭藉,是成就一个风格卓异诗人的重要条件。明清以还许多文学世家的形成、作家的层出不穷,皆与此相关。如桐城方氏、姚氏,湘乡曾氏,南通范氏,义宁陈氏,德清俞氏,无锡钱氏,均诗文传家数代乃至数十代,其独特的文化气质虽尘封于历史的深处,而望气仍可识宝。
家学之外,师承同样重要。传统社会中诗文艺术的学习,是最讲路数、重师承的。清人姚鼐颇为重视的一句话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要“有所法”就得有老师引导,所谓“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潜书·讲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学生通过师承不但可以接受知识,掌握技巧,学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直至“一超直入如来地”;更重要的还可登堂入室,耳濡目染,真切地感受到老师的“身教”。身教是道德的、情感的,也是审美的。在寻常日用之中,即能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尤其是人品。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人品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品才有诗品,有诗品才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诗作才能真正进入审美的视野。很显然,这与那些技术含量既低、人文内涵又贫乏的无所师承的野体,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中国历来重交道。朋友为五伦之一,以文会友是拓展一个诗人成长空间不可或缺的环节。孔子曾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尖,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所谓“群”,孔安国注曰“群居相切磋”。切磋什么?切磋诗艺,研味诗心,交流心得,以匡不逮也。这种广交直谅多闻之友而“群居切磋”的学习方式,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优秀人文传统,影响中国文学发展至巨。钱钟书亦曾说:
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谓“牵率应酬”。
(《宋诗选注·王安石》)
所说既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也有偏颇的一面。事实上这些社交之作并不都是“牵率应酬”、“为文造情”的,更多的应是“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为情造文之作。正是这些交往唱酬活动,造就了大量的诗坛佳话,成就了无数的诗人,留下了众多的名作。如李杜之间、韩孟之间、元白之间、苏黄之间的酬唱,即是如此。杜甫怀念李白诸作堪称千古绝唱。韩孟之间既彼此欣赏,又和而不同,终形成了夐绝千古的诗风。我们从韩愈所写的《醉留东野》中,即可见出这对诗坛石友相与之间是何等的投分: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跨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
而白居易、元稹、李绅之间的酬唱,则推动了新乐府运动的蓬勃展开;苏黃之间的酬唱更是促进了宋诗风的形成,成为与唐诗风并峙的宋诗风的代表人物。即便是钱钟书本人又岂能例外?在《槐聚诗存》序中他也承认:“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尽管说要“概从削弃”,但仍保留了几占全集一半的赠答酬唱之作,由此可见其必有不可“削弃”的价值在。人是有社会性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人性的基本需要。诗人只有广交益友,见贤思齐,才能拓展视野,增进学力;也只有通过朋友间的来而必往的赠送酬答、切磋琢磨,方能激发内在的潜能。没有了交道,诗人还能殚见洽闻吗?没有了友朋的唱酬之乐,诗人还有那么多的激情吗?“概从削弃”这些酬答之作,一部中国诗史还有原来的分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近日拜读黄山书社新出版的《蕉雨轩诗抄》,极有感触。该书作者蕉窗老人刘凤梧先生为当代著名诗词家刘梦芙先生之父,书即梦芙先生亲自编校。梦芙先生编纂是书颇见匠心。正编除编入蕉窗老人自著《蕉雨轩诗抄》、《绿波词稿》、《蕉雨轩联语》、《蕉窗文剩》外,还随相关作品录有诸多师友的评语,而殿以编者自撰《刘公风梧年谱简编》。副编有附录一《刘公显筀年谱》、附录二《遗珠集》、附录三《锄云吟草》,除家谱资料外,主要是选录了刘氏各位先德、后人及著者诗友、学生久经劫难所保存下来的一些零篇散什。从这些入编极富的资料中,可以抽绎出家学、师承、交游三方面的内容,并全面复原造就蕉窗老人这位卓有成就的诗词家的人文机制。下面即以《蕉雨轩诗抄》为主要蓝本来作一个案分析,看看传统的这套人文机制在造就诗词家方面,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为当代诗词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家学:刘氏虽僻处大别山深处,但耕读传家,代有名贤,文风极盛,诗学尤称家学。附录选录诗作者即有刘氏七世祖刘文柯,蕉窗老人曾叔祖刘袖简,祖父刘思振、叔祖刘思翥,父亲刘家晋,叔父辈的刘辛甫、刘焯甫、刘九思,堂兄弟辈的刘国骅、刘国宇,子侄辈的刘梦龙、刘和鑫,哲嗣刘梦芙另有专集《啸云楼诗词》行世。所录诗作皆见才思,足征诗学作为刘氏家学,渊源有自,人才辈出。就中蕉窗老人以上父祖辈诸作,尤见隽才逸韵、卓尔不凡,置之并时各大家、名家集中,亦毫不见逊色。
诗学作为刘氏家学,在培养诗才的方法上,其卓异之处主要有三:
其一,诗学启蒙早。诗学启蒙早反映的是刘氏家族在这个科类方面的精神资源积累丰富,有一整套世代相传、行之有效的传授机制;兼之父祖辈都精通诗学,拥有可靠的家庭师资,并有把诗学当作家族文化血脉自觉传授给下一代以发扬光大的使命感,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便生成了带有文化意味的门风。在这种门风的濡染下,诗人的各种潜质在孩提时代便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并展露出灵光焕发的聪明才智,这是生活在此种门风以外的儿童所远不能比拟的。且看蕉窗老人的自述:
余七岁时,从堂伯父家崇先生入塾读书,至晚归家,夜间灯下,先祖授以五言唐诗一首,琅琅上口,以当歌唱,晓起辄能背诵。阅三载,全部《唐诗三百首》均能记熟。十二岁时,外出就傅,从堂叔祖济川先生读五经,兼习试帖诗,学作五言律,渐识四声五音。偶有拟作,辄携归就正于先祖。
(《蕉雨轩诗抄·自序》)
由于家学优越,故启蒙早,起点高,诗风成熟得也快。老人早年所作我们已无从见到。《诗抄》所收最早的诗系作于1923年的《悲秋》七律八章,其中第一首为:
半生蹉跌误驹光,每届深秋倍感伤。蛮触无端开战局,菊花底事庆重阳?
江流呜咽鱼龙泣,山色苍黃猿鹤藏。闲坐大观亭上望,万方多难又沧桑。
写此诗时作者年三十二岁,方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读书,而诗已成熟如此,直可征见天分之高与家学之力。
由于老人的固守,这种家庭启蒙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仍沿续到老人的下一代。较之乃翁,梦芙先生诗学启蒙更早,这也有他的自述为证:
余出生甫三龄,先君即授以唐人绝句,辄能记诵。……文革祸起,家中典籍悉遭焚掠,仅先君诗稿事先藏匿,幸免于难。余辍学回乡,与农夫牧竖为伍,风霜劳作,饱历艰辛,而每以无书可读为恨。时先君长年卧病,戚友中祝世元、汪瑞芳两先生能诗,每来探访,必有唱酬,午夜清谈,霏微玉屑,余窃听之,遂动学诗之兴。偶于壁罅中觅得劫余之《诗韵集成》半部,开笔试为近体,先君与长兄教以平仄粘对,作十余首后居然熟稔。盖幼时诵诗夥颐,感性敏锐,辨识四声,略无滞碍也。自此为诗一发而不可收,两三年间成七律近五百首,题材则无非四时风物、田园山水之类,内涵单薄,辞气稚弱。所作录呈先君,谓尚有灵气,孺子可教,遂于诗之章法、属对、选韵、炼字,时时训示,一丝不苟,盈篇涂改,墨迹淋漓,余是以稍知诗之门径。
(《啸云楼诗自序》)
《啸云楼诗词》开卷所收为《春暮》二首,其中第一首为:
山林春暖鹁鸠啼,东野烟笼草色齐。松影绿遮荒径外,桃花红到小桥西。
欣迎幽谷新莺至,怕听长堤战马嘶。如此韶光兵未靖,凝眸天际望云霓。
诗作于1968年,其时作者年才十七岁,是一位初中尚未卒业即因文革原因辍学在家的少年。学历虽不高,而学力则富,若此诗,岂是同时大学一般文史教员所能写得出来的,更不要说同年辈那些连平仄尚不知为何物的中文系大学生了。家学之为用大矣哉!
夷考试史,古今诗人的成熟大多有一个过程,即使是天才的诗人也不例外。而有家学的哺育,则可将这一过程大大提前和缩短。袁枚所感叹的“书到今生读已迟”,正可由家学来弥补。蕉窗老人乔梓学诗经历的相似和富有成效,不正证明了家学的重要和在在显示出它的优越之处吗?
其二,专宗唐诗。这可说是刘氏诗学的不二法门。从七世祖刘文柯到蕉窗老人乔梓尽皆如此,可说无一例外。于宋人只重陆游,这大约因陆氏如前人所说的,是宋诗人中最近唐人的缘故。对明清以还各家,也严立壁垒,近唐者间或学之,近宋者则浏览而已。累世相嬗,积累愈厚,风格愈彰。故刘氏历代诗人虽各有特点,而气宇的轩昂,音节的高亮,风韵的超迈,则是共同的,可说一看便知,原则上是不会同他家相混淆的。蕉窗老人之所以能成为现代诗坛“唐风”的代表人物之一,究其原因,这种“专宗唐诗”的家学渊源当是第一性的。
其三,研精七律。蕉窗老人以上刘氏各位先德皆精七律,流传下来的诗作也以七律居多。蕉窗老人虽诸体皆能,而尤擅此体,量大质高,几占全集的大半。其中联章组诗最多,叠友人灯韵诗有至六十五首者,以梅为题的更是在百首以上。所作虽多,而真力弥满,一气贯注,无一懈笔。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在明清诸大家中也是少见的。七律一体对于老人来说直如宜僚弄丸,已入化境,随意挥洒皆成佳构,诚神乎其技矣。老人曾自道个中甘苦曰:
近体诗最难作,更难工。立意要新,措词要雅,押韵要响,谐声要和,用典要切,布局要严,首尾要相顾,中联要空灵,选题要特致,造句要精炼,此其所以为难也。古人云“看来容易却艰辛”,又云“一句诗成百炼锤”,此真富有经验之语,特书之以为初学之诰。
(《见《蕉两轩诗抄》卷之六自注)
这既可看作是老人写作近体的个人心得,也可看作是刘氏家学历世相传的独得之秘。对照刘氏各位先德,尤其是蕉窗老人的七律,是完全达到了这些标准的。席其丰厚,梦芙先生亦独得真传,早年开笔即从七律入手,两三年间竟作有五百首之多,《啸云楼诗词》所收诗虽古近体皆工,而自以七律最精。近时所作已渐臻化境,“寒”韵诗有叠至三十首者,不重复,不趁韵,不做作,移步换形,生面别开,全然不费力气。与乃翁七律相比,蕉窗老人凝炼,允称老劲;梦芙先生气足,尤具张力,此二者之大较也;而整体来说则精神不殊,宗风尽同,韵味均厚。即此可见家学烙印的深刻,及成全诗人所独具的“良法美意”的一面。
师承:家学系统毕竟是相对封闭的,要想大成还得进入更广阔的天地,接受更多的名师指导。不然株守一处,眼光、胸怀、气度、见识、笔力都将会受到限制,而难臻大成。北宋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话: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官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所谓听欧阳公“议论之宏辩”者,即谓亲炙名师的重要。蕉窗老人身丁新旧教育转型之际,私塾读竣,虽年龄偏大,仍不甘伏处乡里“汩没”一生,复入读新式区立高级小学,继之升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直至考入安徽大学,卒业中国文学系。在这相当完整的求学历程中,老人得到了多位名师的教诲,其中在一师时期有精于诗学的胡渊如、高亚宾两先生;在安大时期有精于经学的姚仲实先生,精于词学的李范之先生,精于诗古文辞的潘季野先生,精于选学的刘叔雅先生,精于古诗的陈慎登先生,精于诗史的陆侃如先生,精于词史的周岸登先生,精于新诗和西洋文学的朱子沅先生。其时虽已采用新式学校教育体制,但新式教育的工具性尚不明显,传统教育中的人文传统仍较完整地保留着。学生尊敬师长,师长亦视学生为子弟。讲堂之外,学生复可登堂入室,请业问难;于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仍多情感交流,凡此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人品、文品、诗品的确立。教学方法上,诸师皆为各个门类的行家里手,述而兼作,故指导学生尤为得力。往往片言只语,即可金针度人。我们不妨节录《蕉雨轩诗》、《绿波词》随作品所附的诸师评语,以见个中一斑:
指示门径的:
(陈师评)细读诸作,绮艳清新,兼而有之,他日方驾温李,可必矣。若更进而求之盛唐汉魏,尤致力于古体,波澜纵横,龙虎跳卧,则其自熹者,必又有出乎今日之上者。
(李师评)有沉雄之气,宜多读老杜义山两家律诗,则自无率句矣。
(李师评)似宜专学一家,苦思冥索,必得其不传之三昧矣。
表彰特点的:
(潘师评)佳句联翩,目不给赏,予取其近唐人不阑入宋调者。
(李师评)清新俊逸,兼而有之。
(陈师评)以大笔写小品,极为高格。
(李师评)足征性情之厚。
(李师评)吴梅村此体最工,以作者之才,可以直追古人。
(李师评)作者长于七律,而“桥”、“寒”二韵,尤有丰神。
指出不足的:
(李师评)中四句叠字四见,虽古人亦间有之,究不可学。
寄予厚望的:
(李师评)锲而不舍,他日可望名家。
(李师评)作者诗词均斐然可观,如再下一番苦功,他日必放子出一头地。
(李师评)统观诸作,有辞采,有情韵,有寄托,再于涩字上用功,可望卓然大成矣。
所评各条均要言不烦,直入诗词三昧。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何等的受益,又是何等的激发其志气!其诗品的高洁、气息的渊雅,尤其是晚作所饱含的忧患悲悯意识,似都与这种富于儒家人文关怀精神的陶冶有关。老人于此亦感念极深,曾一再作诗怀念老师,终身都铭记这成就自己的“英年负笈记曾游,风雨挑灯话不休”(《怀潘季野先生》)的美好时光。
交游:相比较近代那些交游遍天下的大诗人而言,老人所交友并不算多,但都极重要。可说优秀作品的产生,相当一部分都与友人间的切磋感发有关。如早年设帐课徒,“得识英邑安君用中、徐君家飏,二君皆工于诗,时相唱和,颇获进益”(《蕉雨轩诗抄自序》)。中年“和宿松王松霞女士步张船山梅花百咏,咸为全皖诗人所推许”(同上),“安徽大学教授徐英(澄宇)先生,评此诗为近三十年之逸品,非新进诗人所能办”(同上)。晚年困居山村,贫病交加,乐与数朝夕者,唯戚友祝世元、同友汪瑞芳、房侄孝哉等三数人而已,而大量饱含血泪之作,即产生于彼此往来感发唱酬之中。由此亦可见老人的厚于性情与富于兴会。李范之先生曾评其诗为诗人之诗,确为深中肯綮的不易之论。相比较学人之诗、哲人之诗、画家之诗而言,诗人之诗是最本色也最难作的。其它三种诗在一般情况下,均可凭藉学问,甚至是挦扯话头敷演成篇,诗人之诗则全凭性情。老人的性情之厚使他笃于交谊,而笃于交谊又激发了原有的性情,给他的交游诗平添几分情感的力量,故读来每每感人至深,交游可说是成就老人之诗之为诗人之诗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蕉窗老人的个案分析,可见家学、师承、交游这一整套人文机制,关系造就诗人至巨。可惜的是,这套机制自“五四”以后就颇受冲击;鼎革以后则全面解体,广陵散绝矣!
如此结局当然是有原因的。宗法制的崩溃,婚姻制度的改革,教育体制的转换,学术风气的转移,职业的分途与工具化,这些直接导致了家族自然遗传基因和人文遗传基因的裂变、流失,家学就此瓦解。师承虽然还有甚至是大面积的,但那是以由表及里皆迥异于人文传统的师承方式存在着的。鼎革以后教育受某大国的影响,全部政治化、功利化、工具化。学校变成了工厂,讲堂变成了车间,教师变成了传授知识的工具,又按一刀切、标准化的模式来批量制造工具,一切都是机械的、先定的。师生陷入一种彼此异化、二元对立的怪圈,没有情感交流,缺乏人文关怀。人文教育的机制成体制性被颠覆了。具体到古典文学来说,情况更糟。在厚今薄古的名义下,这个昔日处于主流地位的学术实体被整体边缘化。在有限的传承空间中,从传承载体到传承方法,政治性、批判性均被摆到了首要的位置。大学中文系教材突出了这一点,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人即讥讽该书专选不好的作品。课外普及读物也突出了这一点,如马茂元的《唐诗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均是。钱钟书所说“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见《模糊的铜镜》),即道出了个中的无奈;马选后来再版时抽换了相当一部分篇目,似也是出于这个原因。除此而外,古典文学教学法更是突出了这一点。传统的述而兼作的教法被抛弃了,传授主体本身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性的病变,新一代的教师、学者大都不会作诗填词,缺乏必要的创作体验。充斥讲坛的是大而空的教条,很少有能落实到作品本身的,不愿也没有能力将批评、鉴赏建立在创作体验的基础上。在这种八股式的教法之下,学生的学力与学历并不完全是成正比的,有时甚至是相反。因为长期机械的教条灌输,会使一个人的思想结壳,并可怕地消蚀掉其灵敏的感悟力和鲜活的鉴赏力。凡此种种,皆解构了传统师承体系的合理构架,掏空了传统师承体系的灵魂。在这种情况下,师承虽存犹亡。
以文会友式交游的消失,则与家学的解体、师承的变异密切相关。后二者的基础地位为以文会友构筑了平台,提示了内在的必要性;失去了这些,以文会友作为群体性的社会活动,也就失去了不可或缺的人文条件,其消失应是必然的。即使有残存,也是零星的、纯个体的,且受制于一定的政治环境。曾几何时,以文字与人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如蕉窗老人与戚友唱酬,即因宵人告密险罹文字之祸,这在极左政治肆虐的时代,绝不是个例。故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个个噤若寒蝉,残存的一点风雅交游活动最终还是难脱被扼杀命运而光沉响绝。
在考察了传统的培育诗人的人文机制的构成和瓦解的内容后,正如上节所说的,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教训实际都已包含在其中了。我想以此作为参照,就重构这个机制,来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想法:
关于家学:在传统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重建昔日的家学已无可能;但亦可参照旧的经验,适当变通。一般情况下,儿童所受的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的。从学习的阶段性特点来说,儿童阶段的特点是记诵能力强,理解能力弱。古人就利用儿童这个特点,专门让儿童背诵,从“三百千”到“四书五经”,皆是如此,且只背不讲。近百年来,新式教育家总是批评这种方式是戕害儿童的天性。其实不然,古人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有经书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经书是很难读的。如果一个人到成年时才开始阅读经书,大量的奇字奥句所带来的生疏感本身就降低了阅读的兴趣和效度;即使理解了,也因旋记旋忘,很难切已体察,变成自己的东西。若早年记熟了,成年再来阅读,即可沉潜往复、从容把玩,无扞格难入之苦,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且经书均属民族文化的元典,中国文化皆从这些元典开出,熟记这些元典是能使人终身受益的。我们现在受某些教条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只让儿童阅读些通俗性的读物,记诵一些简单的儿歌。从短期来说,好象能激发儿童的兴趣;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毫无文化含量和品位的东西记得再多又有何益?现在很多学生书读到高中阶段语文水平还不过关,由于缺少早年的记诵功夫和对经典的必要涵泳,腹中无物,审美能力、鉴别能力都比较差,对商业性的庸俗文风缺乏免疫力,写文章一下笔即油腔滑调,通篇浮词,令人不堪卒读。有人惊呼“误尽苍生的语文教育”,绝非危言耸听。鉴于此,有必要迷途知返,部分地恢复传统教育中儿童记诵经典的做法。果能如此,还得从每个家庭做起。具体来说,可由家长选择一些比较权威的教材,督促儿童从学前到入学后的课余时间里,排日背诵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优秀作品,且程度可逐渐加深。有条件的家庭,对有天分的孩子,可以教一些声律方面的知识,尝试作一些简单的五七言近体诗,以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家学的重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决不可一蹴而就,这只是最基本的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如何重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关于师承:中小学语文教材要进一步改革,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要增加古典文学篇目的比例。写作课要有文言文、诗词写作训练,并逐渐进入高考。而作为先决条件,亦须将中学语文老师的文言文及诗词写作能力,纳入业务考核范围。大学阶段,中文系可将文言文、诗词写作列为必修课,并围绕写作课开出必读书目,鼓励学生多读元典。在目前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下,古典文学的传承要取得明显的效果只能借助这些体制性保障。有体制保障才能普及,普及之下,少数有天分者才能脱颖而出。对于这些少数有天分者,完全可以采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将其推荐给名师,许其登堂入室,作为专门人才重点加以培养。
关于交游:既可以转换成现代的形式,利用媒体、网络,互相酬唱赠答,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结社等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在文化环境宽松的情况下,只要能提高创作水平,各种交游形式都可尝试。这方面的空间,比传统社会要宽广得多,是完全有条件让卓有才华者在这更广阔的空间里,得到更加全面的磨炼,以促成新一代诗人群体的全面兴起的。
结语
诗词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其发育滋长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生态。在经过近百年的重创之后,如何重新恢复它的生机,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尤其是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的今天,复兴诗词艺术这个代表中国文化高度的雅文学样式就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总不能听任诗词艺术日趋衰微,而独举某氏的戏剧小品或某氏的武侠小说来代表中国文化的高度吧。有鉴于此,本文试从两个层面对诗坛生态的构成、破坏进行了探究,并在总结这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构诗坛生态、重新恢复诗坛生机的一些构想。得当如否,欢迎海内学人有以指正。

汪茂荣先生
作者简介:汪茂荣,男,1962年生,安徽省桐城市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学高级教师。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持社社员、中华诗词(BVI)研究院特约编辑、“诗教网”第二届国诗大赛评委、安徽省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理事、安徽省李鸿章研究会理事、“安徽省近百年名家诗词别集丛书”编委、桐城市书法家协会学术顾问、桐城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桐城诗词》主编。著有《懋躬丛稿》,点校出版《睫闇诗抄》、《周弃子先生集》、《海外庐诗》、《诗法通微》、《坚白精舍诗集》、《周退密诗文集》、《唐玉虬诗文集》(后二种与刘梦芙教授合作。以上各书均由黄山书社出版)。主编《安徽桐西汪氏宗谱》。“汪茂荣旧体诗选”获《诗潮》杂志社2013年“最受读者喜爱的诗歌奖”年度金奖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