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台湾来大陆教书后,曾有朋友碰到我北大学生张博,问龚某情况。张说从前欧阳修是“六一居士”,龚先生则是四一:一口台腔,一式衣裳,一张白纸,上课只带一白纸,写几行提纲就讲。可是讲得好,一片文章。
虽是赞美,但显然“一式衣裳”当时足以为怪。所以有学生写信来问是不是戏服,也有人以为我是神父。
乐黛云先生则告诉我:有次汤一介先生要参加个活动,乐先生建议他穿唐装,汤先生还故意抗议:我又不是龚鹏程!
哈哈,是的,我之装束甚是简单,到哪都是唐装布衫,在文化圈中或称奇、或称便、或称好、或来谘询。如刘梦溪先生要去日本讲学,即曾问我如何备一套唐装,以便在正式场合穿。
可是,“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我不像屈原那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年轻时,酒旗风暖少年狂,未必不五色斑斓。
最先的讲究,跟现在的青少年一样。因为衣裤都规定了只能穿校服,故在裤管之长、短、大、小、衣领之宽、窄、尖、圆上略使点小心机外,学生嘛,只能在鞋子上争奇斗艳。
当年台湾全力备战,物资匮乏,没有现在各种名牌、新款、限量版、明星代言款等等。但只要异于同侪、逃离规定,那就是胜利。所以学校规定大家穿皮鞋,我就爱穿布鞋。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黑白帆布鞋,其实就是我们当年的款式,六十年前老古董矣。

但我不喜欢黑的,喜欢一种头略尖的白布鞋。打拳时,活动轻捷、便于使出连环鸳鸯穿心腿。每天把它藏在书包里,进了教室换上,放了学又换回。
等到入了大学,忽然没有了穿衣的限制,倒麻烦了。衣裤鞋袜全成了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很多人都是用高中制服,剪去校徽,先顶一学期,然后再徐图变法。
先是参考校园环境,向学长学习,例如穿长衫。
那是法定礼服,也是抗战以来的老传统,男女都用阴丹士林染成的深蓝色棉布做长衫和旗袍。长辈们习惯这么穿,我们受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教育的青年,也学着穿。以表示文化认同,不跟穿流行市井服装者一般见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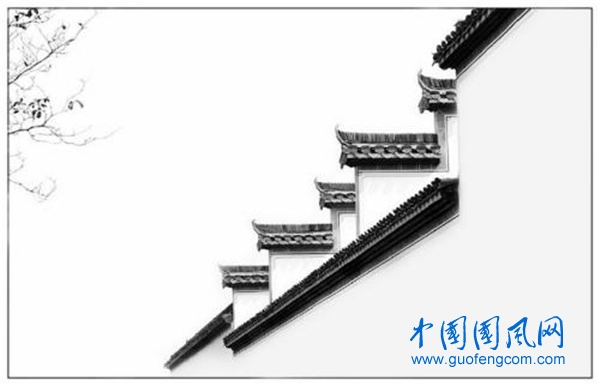
凡校园里御长衫、抬下巴、高谈阔论者,都是这等自以为是的秀异分子,故作鲁迅、陈独秀状。文史哲科系尤甚。一般还有折扇等配件:搭配胡子的,像张大千;啣烟斗的,则似林语堂。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也学将起来。购得一领,穿上,大有刘半农所说:“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之气象。持了折扇去摆拍,又自以为是胡适之。不然则请老师把讲台让出来,由我穿大褂上去开讲,过把瘾。
但既是秀异分子,自不好同俗人抢澡堂、挤食堂、赶公车、逛地摊。长衫在生活上有其需要矜持、不丢身份处,只能视时地而穿,平日常服仍得另伤脑筋。
而男装其实难于女装。色泽有限、款式无多,又没有时尚流行之指引,或什么首饰包帽之搭配,而事实上也没什么选择。卖服装的店家,都只伺候女人,对于男人衣装,则如饲猪,随意扔些杂碎喂喂便罢。只有对女士才会像饭店大厨般,殷勤安排菜品、精心烹调。
幸而年轻男子靠的是可挥霍的青春、自以为是的才华、无穷瞎耗的活力,谁需要化妆打扮,像女人般浪费心思?经常光着膀子呢,衣服多么累赘!
直到硕士毕了业去教书,这才真要考虑穿着的问题。
仍是校园,但须表现有跟学生不同的身份;和老先生们相比,又须显示后进的谦卑。西装和中山装太正式了,平时也穿不住,仍是T恤牛仔裤也不成体统,遂开始穿青年装。
可是穿青年装,有点像情治机关调查员或救国团干部,所以后来又恢复了T恤衫。花的、白的、黑的。有时再套上一件夹克,把袖口拉上半臂。冷静时,戴上墨镜,像个坐在不起眼角落里的打手或杀手。
那些年,在文坛上闯荡,颇有杀气。既呼朋引伴,啸聚山林;也到处写文章修理人,开会,更以得罪人为乐。飞扬跋扈,不知为谁雄。服装,刚好就符合了我江湖人似的气质。
有人以为我有冲劲、能开拓,故推荐我去了政府机关,跟着真正的“大佬”干。这才正式穿起西装来。
西装是我们的标配,整天都得穿,故是常服。出外则又是官服,代表政府的体面,所以也不能乱穿。

可是,你知道的,现代女装,不管哪种款式都要贴身,勾勒胸型、收紧腰身、肩袖紧束,衣服成了一层华丽的皮,缠裹在躯体上。女人爱这样,因为通常意不在衣,只想炫耀身材。男装也这样却受不了,首先是闷,单调。其次是拘束,里面有合体的衬衫、中间有钳束脖子的领带、外有垫肩及扯紧手臂的袖子。把人拘起来,一如官场之拘束灵魂。
我草莽气未除,对此不免适应不良、应对不谨。
有次竟然穿着半臂花T恤就去开行政院院会了。新闻局长大惊,说:“你这……哎,什么时候开会都能这么穿就好了。”我没听出他话中有话,还暗自得意。结果会场果然只适合穿西装,我这短衫根本挡不住寒,差点打起喷嚏来。而且,下午就发了通告:以后不准奇装异服。
马英九兄知道我的脾气,安慰我说平时随便穿无妨,放件西装在办公室,届时一搭即可。
随手搭容易,可是西装更难的是选择。选择什么场合穿什么,其实很有讲究。有次穿了件西装,自以为很精神,结果英九兄很奇怪我怎么穿着猎装来上班。
原来西装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内中颇有区别,跟女人穿旗袍似的。官太太、上流名媛、大家闺秀、学生小清新、酒店招待服务员、妓女,可能都穿旗袍,但剪裁和格式各各不同。不懂的,自以为美,别人则窃笑不已。
西装,有些是中产阶级穿的,有些适合贵族和正式场合,有的还要搭配燕尾服。有的适合轻运动,有的则是平民日常。我们未尝深入西方文化圈,所以经常浑沦不清、自以为帅。
同事们的西装都请师傅量身做,我只胡乱买。这当然常不合适,是以我也想好好做几套。
但后来发现这也不是订做就能解决的。西装本是配合西方人体型及审美而设计的,中国难得有几个人穿得好看,都和西式模特儿身上搭件旗袍差不多。尤其我办大学时期,经常出访,穿西装既旅行不便,跟老外站在一起又容易自惭形秽。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久,想想还是回归汉服为妙。
有次在纽约,要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会晤,而行李延误,无法穿西装。拟陪我去的夏志清教授本来很着急,后见我穿着唐衫来,才松了口气,操着他的苏州口音说:“民族服装嘛,都是可以滴!”

是呀,唐装和长衫都是极容易收拾,出外又什么场合都适宜的。放下袖子是斯文人,可参加国宴,撸起来则可和下里巴人搏感情。民族服装,在国外,更具有文化符号学的意义,极具辨识度,也很容易受人尊重。比邯郸学步,效法欧美人士西装领带、袖扣马甲的,可要简单大方得多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当年熊式一在英国排演《王宝川》时,连续四天,约好的女主角都是来了一天就拒演了。因为熊先生比较矮小,演员有点看不起他。后有人建议他穿长袍,果然因此留住了第五位女主角。而此后熊先生便一直穿着长袍。
熊先生和林语堂先生是近代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之双璧。林先生台北故居之辟为纪念馆,是我主持的,故我也对林先生在海外之一袭长衫知之甚详。这样的事例知道得越多,就越理直气壮地穿着唐装长袍到处跑。
可是在大陆这么穿,倒常有人以为怪了。
曾有少女穿汉服逛商场,群众以为是和服,暴起追打。女孩子逃进女厕所了还不放过,硬逼人家把衣裙脱了,拿出来放火烧掉才解气。
传统文化断层,服饰尤甚,所以才会这样。我所在的文教圈虽然略好些,但穿传统服装,仍会碰到各种不理解。有次去开会,我说刚下飞机,从机场过来。于丹在旁,即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问:“就穿这样,在机场?”另一次,到了会场,王志远兄告诉我:上午议程在人民大会堂,我穿唐装,不让进,说是奇装异服;幸好你没来,否则更不让你进。
一个社会,怎么就混到了把自家服装都当成了奇装异服的地步?
幸而风气渐移,春开不远。
因为受日本动画、漫画、游戏影响的青少年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次元(Two dimensions)架空、假想的虚拟世界,变成了生活之日常,他们也热衷参与大规模的角色扮演(Cosplay)活动。扮成中世纪美女贵妇,和假装是动画片中的人物同样受欢迎。
同时,日本还有“洛丽塔文化”。他们把14岁以下的女孩统称为“洛丽塔代”;并将“洛丽塔”作为成熟女人对青涩女孩的向往的标签,纷纷以电影《下妻物语》里的宫廷娃娃作为标准来打扮自己。
这种文化,跟Cosplay等青少年次文化结合后,先影响港台,接着风行于大陆。等到Cosplay欧洲中世纪宫廷佳人和洛丽塔少女,已成熟套之后,穿个古装,Cosplay唐宋佳丽、大观园十二金钗,岂不顺理成章,更显华彩?
刚好,这时服装时尚界也开始出现了“中国风”的探求。
中国风,是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流行,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器用,服装之面料、图案、纹饰、花色、式样等都大量吸收中国元素。但晚清,中国“同治中兴”开始学西方以后,西方也就渐渐转向,从日本学得他们所要的东方元素,自1875年以后,开启了现代服装的新纪元。
中国人食衣住行反而都努力学西方,穿上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服装,出现了我前面所说:以传统服装为奇装异服的现象。
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重新崛起,世界服装界的眼光也再度关注回中国,中国风作品又在时尚界设计界翻红。国内的纺织业、设计界,想建立中国服装品牌的时机乃渐渐到来。
相关机构和企业,在企业变革、网络营销、跟风学习西方设计与时尚服装之外,亦不能不开始探讨文化与服装的关系,回头去了解传统服装、研究中国服装的体系和样式,希望能找到新路。
毕竟,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的同质性越来越大,若不能显示自己的特殊性,就“泯然众人矣”,故生存之道只能是发扬其传统文化特性。

这种新的时代形势和需要,自然也带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
例如我在台湾时,台湾固然也每年祭孔,但年轻人Cosplay,我和台北市政府也Cosplay。在市府大厅演戏,由我扮演孔子,教诲一众弟子。然后孔子誕辰祭孔仪式结束后,还要利用祭台,我来导演一场正式的儒学讲会。官员和群众礼乐陶冶之后,皆席地坐听之。
后来我在都江堰等地办孔庙、在杭州等处办书院,可说都是这活动的延伸。着古衣冠、复原古礼、钻研古乐,铿锵揖让,吉军宾嘉,祭如神在,好不热闹。在演礼演戏之中,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也就逐次恢复了。
你说这是复古吗?当然是的,恢复了不少。但只是复古吗?不,主要是呼应时代的需求、探索全球化时代我们自己的定位、也参与了新汉服的设计。
其中,有些古风不可能恢复,也不会有人去恢复。例如唐宋人男男女女都要簪花,簪到“菊花须插满头归”、彷彿一棵樹的地步。虽也好看,就至今无人提倡。凡提出来的,都有现实上的指向。
像现在的大学生毕业袍,其实原是西方修道院的修士袍。西方大学,是由教会修道院发展来的,故这样穿很合理;我们也模仿他们这样穿,却实在莫名其妙。我在办大学时,曾经另行设计了一套。后来江苏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也让师生及教育部官员,男的穿朱子深衣、女的穿曲裾。这就都是批判现实的托古改制。
而且“深衣”是个复杂的问题。它以“被体深邃”得名,但只知是衣和裳在腰间缝合,而其款式其实已不可知,所以朱子、黄宗羲、江永、戴震等等乃至日本儒者考证复原,聚讼了上千年。
现在依考古所得,认为深衣是采用绕襟裹身的方式穿着。由于紧绕身躯,衣内虽然会再穿裙或绔(不连裆的裤子),但在外观上并不明显,可能只在衣身最下摆露出一点裙缘而已。
但这样穿,现代人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汉服运动者多半采取朱子的复原款。

而这样的深衣可以做为典礼的礼服吗?那又未必。因为只是古代诸侯﹑大夫的家居便服,到唐朝仍只是朝服、祭服的中衣,还不是礼服。庶人百姓钱少、阶级低,才会以此为礼服。但像婚礼,就仍要“男着衣裳,女穿深衣”。
可见真要复古是很难的,会陷入无尽的“学术”泥潭里,继续聚讼。大家只要心知其意就好,不必纠缠细节。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吵架,而是借此为故国招魂、同时也为我们的时代做点有民族文化意义的创造。
这样说,穿个衣服又竟有绝大的意义,感觉跟披上铠甲要上战场似的。
对呀,也没必要如此!穿衣吃饭,自然为要。以上说的只是“民族、身份、年龄、场合、角色不同,着装自然不同”这个道理而已。我自己以这种自然自在的方式穿衣,也不愿勉强别人。
因为不同民族、身份、年龄、场合、角色穿不同的服装,实质上就是演戏。都是为了适合剧情的假扮,人却还是那个人。不会因戴了王冠,身上就能放光,但王冠仍然每个国王都要戴。天地大舞台,服装从来不是为了实用的。
所以现在各地都办汉服节就甚好。节日是特殊的日子,反日常。例如平常上班工作,节日就可放假、休息、玩乐。可用理性彰显日神精神,找回自我;也可迸发酒神精神,放纵自我。现在的汉服节,就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既属于时代潮流新势力之一环,又是异端、游戏与玩乐。游园、游湖、游街、游玩、化妆、摆拍、自拍、花枝招展、花团锦簇,而亦演礼亦作乐,亦投壶、乡饮酒,并濡染茶道花道香道射道等等。将来能否“技近于道”虽不可知,现在却已可得浮生之乐了。
人类从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资本时代、资讯时代,渐渐就要走入游戏时代,汉服节或许就是一个入口。
因此,五月一日我将在陕西汉中“兴汉圣境”主持汉服文化节,先玩将起来。五一是国际劳动节,所以我们要用游戏精神来调剂它。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天还是国际示威游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Day或者May Day)。因而我们也要来一场服装的游行示威,脱我工作服,着我旧时裳,给世界一点颜色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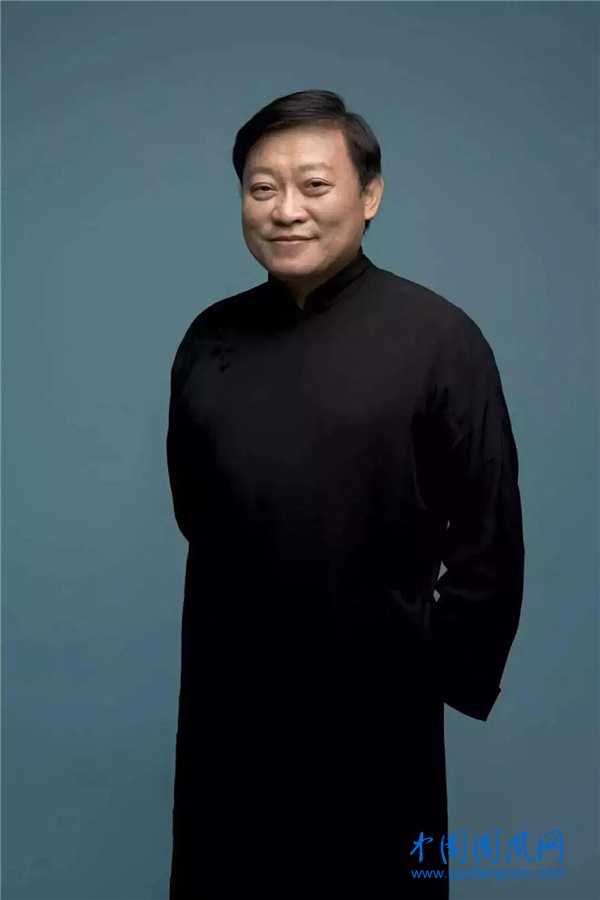
龚鹏程先生
【作者简介】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