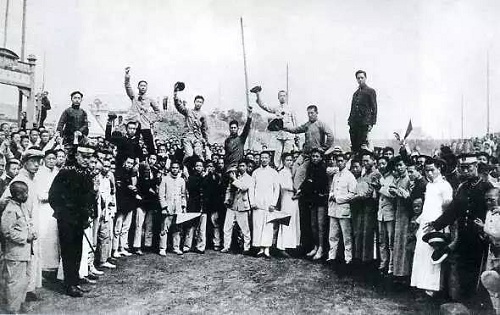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罢科举、设学堂,整个中国教育结构,彻底翻新。
学堂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一切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不必再强调。
学堂教育的另一性质,则在于它的浅易。因它是公众教育,所以有些学堂又称“ 公学”。是针对普通大众的,故为普通教育,“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因此其教材及教学内容都要浅易。所以只让学生“学作日用浅近文字”。
当时舆论也都主张如此,如次年《时报》便主张“小学者,授人以浅近之普通知识与浅近之普通文字者也”,故宜“ 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并诸修身科目,复撰读本,以授普通知识与普通文字”(五月廿二日)。
五四运动,放在这个时代环境中看,似乎就可以看成是普通、国民教育向大学高等教育的延伸。
因为中小学教育虽然改了,大学毕竟不比中小学,社会期待较高,博学硕儒又仍群聚讲贯于其中,是讲经典、重博学深入者之根据重地。像桐城古文派的一批耆宿,如吴汝纶、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等,就在北大。他们所讲,终究仍是古昔至深极奥之文学。校中林损、陈汉章等经史名家,又岂肯以浅俗文学相教授?
胡适、陈独秀等人,正是处在这种气氛底下,才激发起了改革,拟“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深的山林文学”,建设平易通俗的国民文学。
他们那追求国民文学化的文学革命,遂在许多地方都体现着国民教育的气味。
1917 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后,接着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强调要建设“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宣称二千年来的文言文早已死去,只有白话文学方可依循发展,谓宜多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以为模范。
钱玄同及刘半农继起,认为“世界事物日繁,旧有之字与名词既不敷用,则自造名词及输入外国名词,诚属势不可免”(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 ,“ 废汉字,以拼音文字代之”“ 废汉书,悉读西文原书” ( 钱玄同《中国今后文字问题》)。
这些言论,跟国民教育实在关系密切。胡适的主张,其实就是国民教育对于小学生写作文的要求。
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词句,备应世达意之用,自然不可无病呻吟、堆垛典实、套用熟调、摹仿古人。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
特别是“须讲求文法”一条,历来论者都不明白胡适为何特举此为说。但若溯考小学堂之作文教学,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义于斯。
《奏定初等学堂章程》即规定中国文学课程“ 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实际教学时,则是以口语教学生连缀成文。因此对于如何符合文法地构成文句,甚为重视,故“中国文字科下注云:讲动静虚实等字法,并句法章法缀法书法”。
当时舆论,亦对此格外强调,《时报》即主张“文法则由各品词,以至单文;由单文以至复文”。另因英文课甚重,据赵宪初回忆,南洋公学附小须读《纳氏英文法》四本(《我所知道的南洋模范中学》)。可见文法教育在整个小学堂教学中是极为吃重的,教中文,实际上便是学习着教英文的方法,由文法入手。
依学制规划者的观念,大学也还是要讲求文法。故《奏定大学堂章程》明定中国文学研究法为中国文学门之主课,其内容之中,便应讲授“ 东文文法”“泰西各国文法”。胡适特别把这点提出来,正符合政策,可以充分表现学堂教育的特性。
其实中国古代哪有文法?所谓文法,是清末马建忠仿效西文文法造出来的。小学堂视此为学文秘径,刻意强调,直到现在。
胡先生八不主义中又有“不讲对仗”之说。胡适本人固然不喜欢律诗,但这一点亦小学堂教育之特色使然。《奏定初等学堂章程》即曾云: 初等小学堂读古诗歌,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唯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但万不可读律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读古诗歌五七言均可。⋯⋯其有益于学生,与小学同,但万不可读律诗。学堂内万不宜作诗。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也都抄这段话。我们不知为什么订定学制者如此重视这一点,反复强调,而且用了“ 万不可”这样的字眼。但学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传统、新的特色,不作律诗、不讲对仗了。
如此八不,目的是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国语,自然也是学堂教育的重点。
光绪廿八年(1902 年)吴汝纶就向张百熙推介了“言文一致”的日本教育,主张推行简笔字、实施国语教育: “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进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其法用支微鱼虞等为字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
此文所提“言文一致“之原则,后来成了五四文学运动中的主要观念。省笔字也被发展出来,形成后来汉字拼音化、文字简化的运动,影响至于今日。
光绪廿九年(1903 年)张百熙、张之洞未采用吴汝纶发展的简笔字的建议,但采纳了他发展国语之主张,于《 学务纲要》中明定:“ 各学堂皆学官音。”后来的国语运动,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胡适的主张,亦是如此。他所采取的文学语言,亦以北方官话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话文学为基底。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另也有一大半有取于先秦以迄唐宋之浅易诗词歌谣。这部分,显然也還是可看出有中小学教育的痕迹。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云: “小学中学所读之诗歌,可相学生之年龄,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读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
这样的书单与教学内容,和胡适所选取的作品不是非常非常雷同吗?这未必是胡适沿用它,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想:此种小学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感性、品味及欣赏能力,对胡适实有深远之影响,使他在面对我国文学传统时,主张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且较为欣赏乐府歌谣谚语。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1918年《北大日刊》便展开征集歌谣的活动,后来出版了《歌谣汇编》《歌谣选粹》,则更可见此类影响并不只在胡适身上起着作用。
除了体制之外,讨论小学堂与五四文学运动之关系,还得看风气。
前面说过,学堂基本上是洋气的,因此光绪廿九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奏请递减科举时,便提到反对者认为“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对于此种批评,张之洞等人一方面要与之对抗,肯定办学堂的必要性,一方面也不免回过头来,要求“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戒袭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须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 ⋯⋯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学务纲要》)
这里显示了两种态度,一种即是那习气濡染下的少年,不但外国名词谚语袭用于不自觉之中,甚且借用“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后来如傅斯年主张“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和一切修辞上的方法。 ⋯⋯务必使我们做出来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 怎样做白话文》),即是此类风气之波衍。
另一种态度,则是认同张之洞、张百熙的。认为中国既有通用名词,何必袭用洋文。刘半农就是个例子。刘氏担任国立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曾禁止学生间互称“蜜斯”,规定以“姑娘”代替,引起轩然大波。《北平晨报》甚至出过一期《蜜斯和姑娘专号》来讨论此事,《世界日报》《大公报》也都有人撰文抒论,亦有人开玩笑谓当把“ 蜜斯特”改称为“ 姑爷”。 刘半农乃辩解云:“女子称谓之名词,国语中并不缺乏,为保存中国语言之纯洁计,无须乎用此外来译音之称呼。”(1931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他的说法,又多么像张之洞、张百熙呀!
例子我不多举了。总之,五四运动的许多问题,要从清末民初的中小学堂教育去看,才能理解是无疑的!
五四运动,曾被类比为西方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我也同意这种类拟,但所谓启蒙,或许应该另做解释。因为:启蒙,中国传统上就指针对小孩子的开蒙之学,一般称为“蒙学”,用以启蒙。而五四运动之兴起,便可视为清末小学启蒙教育向大学的延伸发展;其内涵,也不脱蒙学教育之色彩。
启蒙教育,是使人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教育,所以要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浅易的教科书,将之编组为一套浅易知识,授予接受启蒙的小朋友。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小说史略》等等都具有这种性质。把各种知识及传统事物,重新简化,构成一个简单的系统,俾便掌握。
晚清之启蒙教育,本身又是对传统私塾义学蒙馆的反动,具有改革旧制、讲授新学,以使被启蒙者认知世界新局势,接受现代新观念之作用。如此启蒙,亦正为五四运动之鹄的。
在这种教育改革运动中,不只蒙学堂、小学堂属于启蒙教育,整个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其实就是着眼于启蒙的。因为改制的起因,就是感到国民普遍无知,以致国力衰微。惟有推动教育改革,充分启蒙,方能使一般国民“知书”“达礼”,进而强化国力。
因欲使民知书,故启蒙教育须提供基本知识,例如使人民识文字懂算术,略晓史地理化等等。因欲使民达礼,摆脱椎鲁粗俗的生活,故启蒙教育又须提供国民基本教养课程,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五四运动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因欲使一般国民均能享用文学、使用文学,故提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因欲使一般国民都能具有文化教养,故五四运动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认为当时男女仍多兽性、奴隶性,须渐渐转移风气。而其目的,则也是希望借此以强国。
这也可谓以浅俗进行整体社会的教育改造。古人反对“以艰深文其浅陋”,五四新文化诸公的努力则是“化深刻为浅俗”,要把一切都“拉下神坛”。
然而,它提倡之新道德新思想,系参酌西方而得来的,不免被反对者指摘: “不奴隶于中国,转奴隶于外人”。它那简易浅显的文字文学及思维,又到底是启蒙了理性,还是把大学办成了小学蒙馆呢?
看看五四以来的大学、看看五四以来的思想界,你一定会有答案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