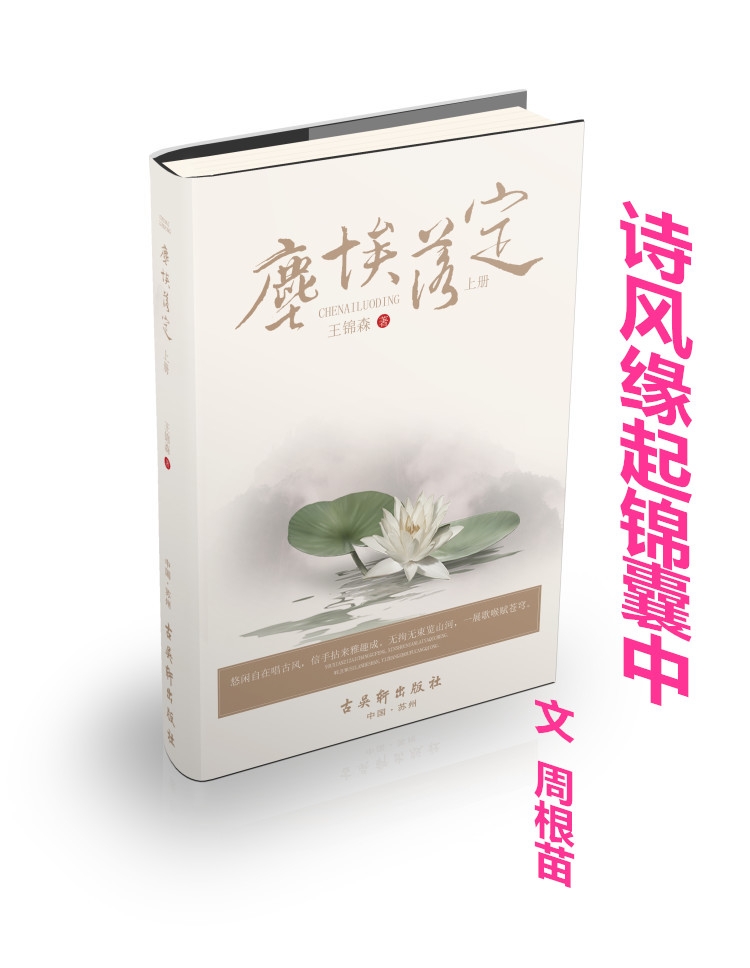
——王锦森诗集《尘埃落定》初探
一
当我从王锦森先生手中接过那厚厚一摞名为《尘埃落定》的诗稿,既惊讶诧异,又惊叹不已。2016年12月,他那凡六章、计600余首的诗词集《红尘行吟》(上、下两册)付梓出版;2017年12月,他那凡六辑、计500余首的诗词集《坐看云起》(亦为上、下两册)又结集面世。这才两个多月,一部近500首的诗词作品集又脱稿杀青,莫说倚马可待脱口成章,别论才思敏捷笔走龙蛇,如此的创作速度,在我熟知的诸多文友当中,堪称神奇了。何况他的主业是从事新闻写作,在漫长的40余年的记者生涯中,虽然他的兴趣也曾涉猎戏剧、电视、散文、小说等等领域并小有成就,但他的诗词创作居然独树一帜斐然可观,作为往昔共事多年的同仁知交,不由我不刮目相看暗自惊喜惊羡。
检视这部近500首的诗词作品,只有寥寥几首是昔年旧作,百分之九十九的篇章均为2017年8月至2018年春节期间撰写。其间,锦森先生几乎每天都有一至两首、三首诗词脱手,其中2017年8月24日一口气写了13首,9月29日写就7首,即便在2018年春节期间,他每天也雷打不动见缝插针,大年三十他撰写了4首,正月初一出手5首,区区十来天的时间,数以十计的诗词,竟如山涧清泉一般,从他的脑海里哗哗泻出……常言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能补拙功在不舍;勤奋出成果;勤奋造就“天才”。王锦森先生的实践,再次印证了人世间这一显浅的道理。
二
捧读《尘埃落定》那洋洋洒洒近500首诗词,其引人思索引人感悟引人共鸣的特色多多。统观全篇,其师古也好,其创新也罢,笔者以为以下几点特色较为鲜明突出:
其一,《尘埃落定》在形式上师古而不泥古。
锦森先生的《红尘行吟》《坐看云起》和即将付梓的《尘埃落定》均为古风体的诗词作品,但和严格的古风体又迥然有异。诚如耿汉东先生在为王锦森先生的《坐看云起》诗词集撰写的序文中所言,仔细读来,锦森先生那些诗词作品与古体诗还是有些区别的,“他不遵循古体诗的平仄格律,多有出律,且有破格变格,它是古体诗的改革族,是一种新古体诗,用几句话来加以概括:采用古诗的句型;大体押韵;不讲究平仄;句式不一,体裁(题材)多样;使用当代语言,有时代气息……”窃以为,耿汉东先生所作的这种定义精准到位,笔者亦有同感。众所周知,我国古典诗词有关格律、声韵的程式,包括平仄、对仗、押韵等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譬如七言律诗,皆由七言八句所构成,中间四句为骈偶句,必用对仗方合规矩,平仄、对仗、押韵等等均为最基本的要素。在漫长的岁月中,锦森先生虽然焚膏继晷博览群书博闻强识经年不辍,深谙我国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元曲之要义,但他师古并不泥古,师古亦并不循规蹈矩。他笔下的诗词作品,大多并不遵循古典诗词必有的平仄、对仗等等程式,而往往是独出心裁独辟蹊径独具创意。他将“文学从不遵循凋敝的规律”这句名言奉为圭臬,反对用形式束缚内容,尽力避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因循坐误因词害意,诚如他自谦所言:“平素所学有限,诗词格律难以驾驭,且亦不喜死格僵律所规限,故所吟唱诗词多有出格出律之处。睹物言情,酣畅为快……只想在有生之年,拾掇点文字结集,用自己半生浅显的见识与感悟,仿古风诗文形式,以明心见性之白话,授人以渔。从而给后人留下点开智启慧的善缘。亦不负初心,不负所愿。”
话虽如此,但以愚之见,锦森先生的不少诗词作品还是承继了我国古典诗词的一些优秀传统。譬如,在作品中灵活运用典故乃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它不仅深化了诗词作品的艺术内涵,强化了诗质意蕴,也大大增强了诗词作品的美学功能和传播效果。仿效古人活用典故,在锦森先生的诗词集中不乏其例,如“高山流水琴悠扬,伯牙子期佳话长。人间知音最难觅,一曲广陵断嵇康。”(《午后听琴即兴》)短短四句,述说了我国古代两个著名的典故,读来让人回味怀想击节抚叹;又如“廉颇虽老尚可饭,黄忠八十大刀旋。莫道黄昏无秀色,夕阳蔚霞正满天。”(《诗和伟弟文》)仅仅七言四句,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古代两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老英雄形象,描绘了一幅人至晚年彩霞满天的绚烂图景,其乐观豁达意境跃然纸上!
作诗填词应当押韵,这也是我国古典诗词一个最基本的特征。诚如国学大师王力先生所言:中国的诗歌,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歌,甚至民歌都要押韵。我国最早的古诗大约源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发明的劳动号子,当事者在辛苦劳作时引吭高歌,直抒心中块垒,以消解艰苦劳动的疲累。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些劳动号子由于好听好记,后来经文人创作演变为诗歌,其落脚点还是以诗为歌,以演唱形式而流传,亦有论者将古诗词定性为声觉艺术,想来也是有迹可循不无道理。而锦森先生的诗词,也大体上遵循了这一古老的传统。如“咬文嚼字非吾求,遣词造句应自由。莫让陈规陋习困,随喜即兴唱春秋。”(《与诗词众友取乐开心篇》)又如“迟暮西山唱黄昏,日久情深恋故人。往事如烟随风去,功名利禄化浮云。”(《品茗悟道》)诸如此类,读来琅琅上口清晰响亮,其韵味其意境其节奏感其流畅感,可让读者口诵心惟口口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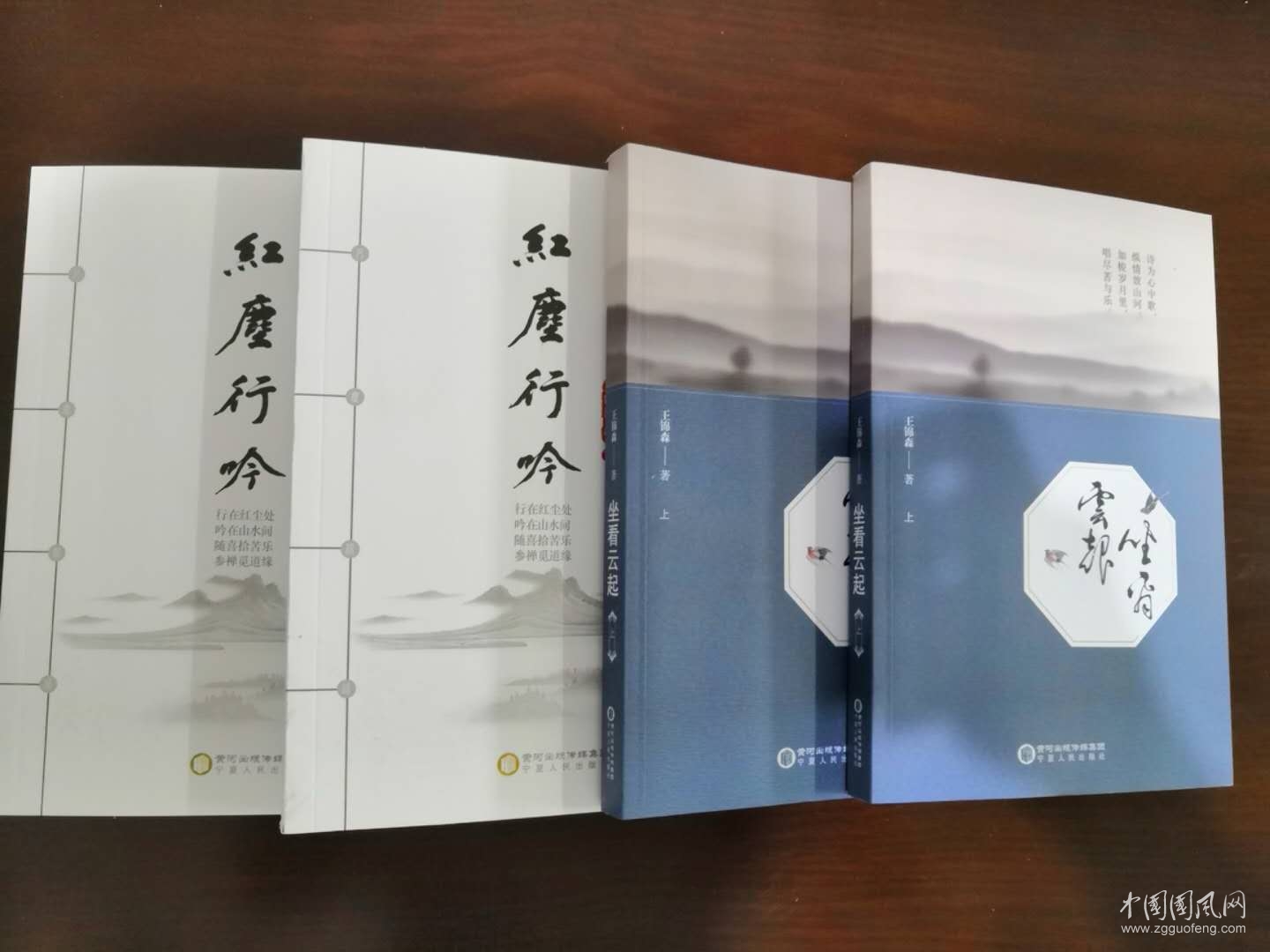
其二,诗词题材丰富多样,诗词内容森罗万象。
锦森先生是省级媒体的一名资深记者,写了一辈子新闻,当了半辈子驻地站长。说他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社会发展的记录者,时代激流的弄潮者,形形色色群体生活的感知者,实不为过。得益于其记者的身份职业,他终年累月奔波于上至高府深院,下至田间地头,目击耳闻大千世界社会风云自然景象各色人物,加之这位有心人博学多才博采穷搜博物洽闻博闻强记“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其诗词题材的丰富广博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撇开已经出版面世的诗词集《红尘行吟》《坐看云起》不说,仅就即将付梓的《尘埃落定》而言,大到国家隆盛,小及百姓庸常,其笔触涉及历史记忆、时代发展、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小桥流水、花鸟虫鱼、偶发事件乃至日常文朋诗友聚餐品茗习字赏画等等方面。常言道:生活之树常青,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人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亲历者的身份,以个人直接生存其中的周遭环境为背景,以一人一事一物一景为由头,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善恶美丑等等内容融注于诗词之中,不仅使这部诗词作品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广阔视野,也使这部作品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民生,凸显了作品集的艺术魅力和整体分量,让人读后在潜移默化中获益匪浅。

其三,用真情实感凝缩优美深邃的诗行。
情感真挚历来被视为诗文的灵魂。古往今来,文坛的大家巨擘均十分看重诗文中的真情实感。“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唐·白居易语)人间难得是真情,“无情未必真豪杰”(鲁迅语),因而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语)。事实上,缺少真情实感的作品,等于缺少了灵魂;没有灵魂的作品,则犹如假人假面,即便衣饰再华丽再光鲜,也只是一具没有血肉没有生命气息的花架子而已。因而,时下一些拿腔捏调矫揉造作虚情假意无病呻吟的诗文,只能让读者味同嚼蜡索然败兴。然而,锦森先生的诗词作品,没有那种缠绵悱恻的低吟浅唱,没有那种无病呻吟的凄切凄凉,没有那种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譬如:“河东河西三十年,炎凉世界不同天。人往高处水流低,花开花谢无须怜。当年少壮气宇轩,不慕权贵不羡仙。凛然正气写春秋,碧血丹心照云川……”(《有感纸媒风光不再》)譬如:“铁骨擎云天,豪气冲霄汉。为民张正义,碧血唱浩然。”(《观微信真英雄——崔永元》)又譬如:“一池荷莲香韵浓,随风摇曳绽玉容。始自污泥身不染,清风明月送嫣红。”(《观荷赏莲即兴》)……如此等等,看似随感即兴,其中却饱含大众百姓的良知共识,抒发了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大爱情怀,从中可以窥见一位崇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新闻战士的赤胆忠心坦荡胸襟,一位生活强者时代歌者纯真质朴深沉丰富的情愫,其溢于字面的忧患意识,其隐于诗行之中嫉恶扬善求真尚美之心彰明较著,从而无声无息地滋润着读者的心灵,进而引发读者的共鸣,这大约便是“文以载道”产生的正能量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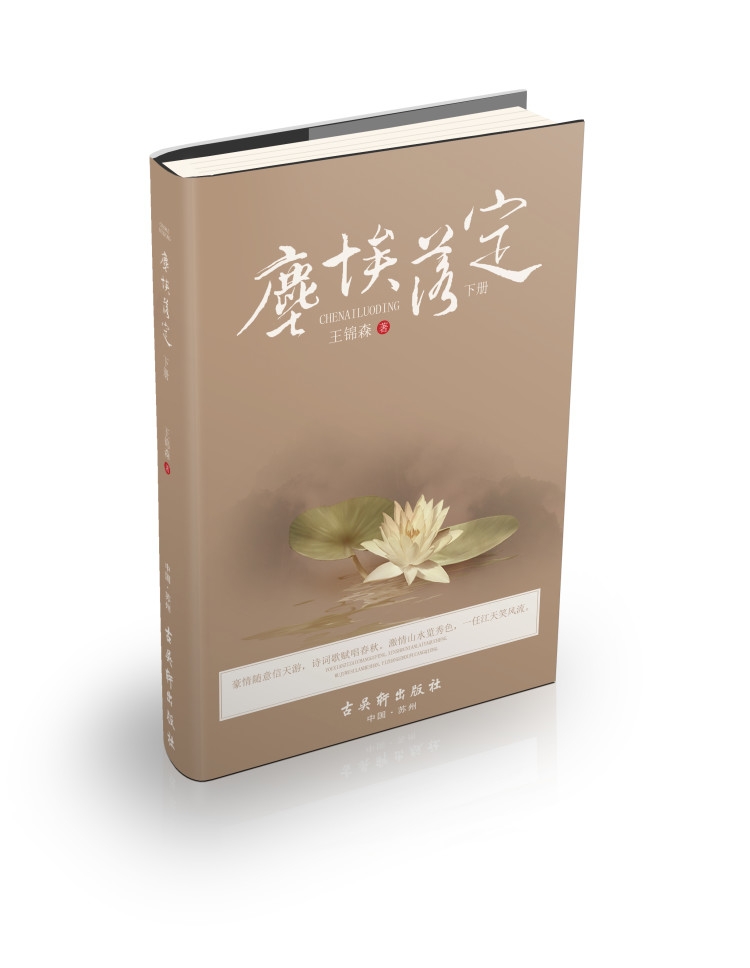
其四,诗词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自然也是诗词的第一要素。古人作诗,十分讲究语言艺术,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前蜀▪卢延让语),“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唐▪顾文炜语),“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语),“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语)……这方面的动人事例,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正是得益于古代文人遣词造句的功力,我们现今才能拥有那么多百读不厌名垂青史的千古绝唱。令人遗憾的是,现今有的作者空腹高心自命不凡,一味在作品中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地卖弄文采玩弄辞藻;有的作者偏爱生僻拗口晦涩艰深佶屈聱牙的语言,硬是把自己的作品捣鼓成当代人读不顺看不懂想不明白的“天书”,却还振振有词大言不惭地宣布,他(她)的作品是写给后世人们阅读欣赏的……凡此种种诞妄不经,不能不让人摇头叹气!然而,锦森先生虽然拥有较为厚实的古文功底,其在诗词作品中运用的语言却和上述作者大相径庭。研读他的诗词作品不难发现,他的诗词语言深入浅出生动鲜活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他的语言形态注重口语化讲究质朴流畅,诗词中经常出现日常口语、方言、俗语、行话乃至一些广告用语、网络流行语,显得十分大众化。美国当代诗人肯宁罕穆曾经说过:“我把诗当作一种说话方式,我以诗行说话。”无独有偶,锦森写诗,实际上也是在用诗行说话。譬如,他的诗作“春风吹拂百花香,花间蜂蝶枝头忙。采得花粉酿琼液,送予人间润福祥。”(《观“春草图”即兴》)譬如:“大师信口开闲篇,话糙理明日月悬。怡情养眼生稚趣,悠然自得乐翻天。”(《诗协群中开心取乐小辑之十一》)又譬如:“呼朋唤友聚庐州,待客宴宾同庆楼。美酒佳肴满堂彩,最是可人红烧肉……”(《午时与友人相聚即兴》)……这些诗作,言之有物,言之有文,言近旨远,脍炙人口,识文断字的读者一听就懂得,一看就明白;听后很亲切,看后能记住。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唐代那位毕生追求诗歌语言大众化的大诗人白居易,白老先生的诗作曾经“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乃至“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白老先生的一首诗,竟然可以换来一条胖头鱼一挂五花肉,以至当年老先生在世时,他的粉丝拥趸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引车卖浆者,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大江南北无处不在,千年以后仍被后人公推追捧为中国诗歌大众化无出其右的典型代表,个中主要缘由,不就是因为白大师的诗作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从而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与大众百姓情感相通、生息相关、声气相连、心神相交吗?当然,锦森先生和白大师远不在一个层次上,拿两者的诗作语言说事也有乱扯之嫌。不过,锦森先生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一个诗歌爱好者,仰慕大师,见贤思齐,从白大师的创作实践和累累成果中汲取营养得到启发获得教益,从而更加坚定诗词大众化的信念,日后在创作中让自己的诗词语言更“接地气”,更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津津乐道乃至口口相传,倒也可以树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三
倘若以为锦森先生的诗词作品已达炉火纯青至臻至美之境界,肯定有过誉之嫌,与事实也存在很大距离。相信锦森先生也不会认同这样溢美的评价。
实际上,锦森先生并非正规的中文科班出身,在几十年重务缠身的人生经历中,他也从未得到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其业余时间痴迷的诗词创作,一则源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二则有赖于自己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苦读苦学苦钻苦练,加之有的作品脱稿仓促推敲不够,因之,他的一些诗词作品显露的欠缺不足也清晰可见在所难免。譬如,有的诗词作品立意显浅意象模糊,有的情感干涩寡淡少味,有的语言形似标语口号,直白有余含蓄不足,如此等等,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作品意境的深化,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进而影响到整部作品的艺术价值。虽是细枝末节瑕不掩瑜,但毕竟让人读后生发遗珠之憾。学海无涯,学无止境。坚信锦森先生在日后的创作实践中,会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耕耘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剔除创作中存在的软肋,获取更多可圈可点的硕果!
是为序。
【作者简介】周根苗,安徽日报社原编委、新闻业务总监、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