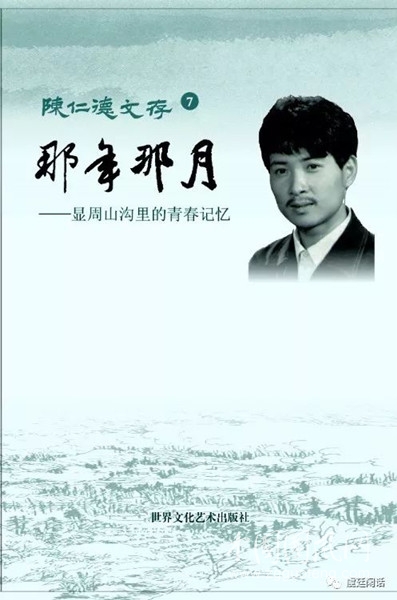
【8】办政治夜校
在勒紧裤带学大寨的日子里,我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组织社员们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和“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吴家场上的农民们基本不识字或者识字极少,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年年月月周而复始,对山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遑论整个国际社会。在极度封闭的时代,即使是农民中那些极有智慧的人,也无从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对于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了解,就是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本来,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知道“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没有必要去知道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他们祖祖辈辈都平静安详地生活在这块群山环抱的家园里,他们虽然有贫困、疾病和烦恼,但是也有自己的快乐,并不像有些人反复鼓吹的那样长期生活在阶级压迫和剥削中。1949年以来,不知政治为何物的他们,被无情地卷进了政治漩流中,他们的一切都和政治捆绑在一起,不再享有宁静的牧歌式的生活。在“翻身做主”的光环笼罩下,他们开始忍受前所未有的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役,不仅如此,他们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迫去“学习”那些与他们毫无关系的走马灯一样变着花样的“政治理论”。现在,轮到他们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了。
按照当时最吃香的做法,组织学习叫做办政治夜校,教室是现成的,就在安乐小学我住的房间外,教材也是现成的——“马列的六本著作”,教师当然就是我了。我是队长,又是公社派来的,在吴家场无疑也是文化最高的人。
于是,在一个黑沉沉的夜晚,安乐寺的教室里点亮了几盏油灯,二十多个人坐在我的面前,听我讲“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
自成年以来,我就对什么“光辉理论”之类的东西缺少兴趣和研究,而且,我自己确实也非常肤浅,中学只上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没有读过什么书,对《巴黎公社》《法兰西内战》什么的根本不知道。但是我毕竟还认得些字,赶紧把那些书看看,也就知道了什么“茹尔法夫尔”“梯也尔”“俾斯麦”等等。可怜的是我面前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起,甚至根本就没有名字,现在要他们来听这些“光辉理论”,简直比听天书还难。但是,毛泽东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他们就没有理由不知道。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看见60多岁的刘松云也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里,一种莫名其妙的目光从他模糊的眼眸中透出来。他显然想努力地听懂什么是“茹尔法夫尔”,但是完全没用。看得出来,他吃力的程度远远胜过了开山打石头。
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喜剧的事情之一,一个根本不懂的人很认真地在上面讲,一群根本听不进去的人在下面很认真的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所有荒唐都极其庄严地上演着。
这样的夜校当然是不能持久的,和那时所有昙花一现的“新生事物”一样,办了两次后就再也没人来了。
【9】重返吴家场
几十年来,我辗转江湖,形如飘蓬,走过不少繁华美丽的地方,但是破烂冷落之极的吴家场却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有时甚至会出现在梦中。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回过吴家场,我还没有走到场口,就被在坡上劳动的人认出了,他们放下锄头,拉着我的手,说不完的话。那天,我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是:
依依昔日景,眼底认分明。落日满山岭,悠悠总是情。
九十年代,我在重庆采访市委副书记甘宇平时,把我的诗集《云气轩吟稿》送给他作纪念。不几天,他叫秘书给我送来了一幅他的书法作品(他的书法较有品位,重庆很多地方有他的题字),四尺整宣,打开一看,竟是上面这首诗。我的诗集里有几百首诗词作品,他怎么就选出了这一首呢?读着甘宇平书写的条幅,我眼前又出现了吴家场,那个我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地方。我总想回去看看,去看看那里的老乡,看看那里的田园,看看那个仿佛化外之地的小乡场。
2013年7月23日,气温逼近40度,热浪排空,炎光四射,我冒着酷暑,不听人们的劝阻,重返魂萦梦想的吴家场。
此时的吴家场已经不再叫安乐8队,安乐大队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以前属于显周公社的安乐大队整体划入了拔山镇芋荷村,安乐8队已经成了芋荷村的一个社。显周公社也早就从历史上消失了,靠近拔山的老鹰、安乐划入拔山镇,其余全部归并到了花桥镇。
从显周场到吴家场,不再像以前那样徒步,一条约三米宽的村级水泥路已经通到安乐寺门前。我刚认识的一位在拔山场上经营手机的老板罗某非常热情地开着长安车送我,显周完小退休老教师,我的老朋友黄天雪邹道权两位全程陪着我。村级公路坡陡弯急路窄,汽车小心翼翼地游走在险坡高崖上,幸而罗老板车技不错,那条村级路上仅有我们一辆车,所以一路还算顺利。
汽车越过一道道山梁,山顶豁然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用条石砌起来的大院,我脱口而出:“这不是安乐寺吗!”真是安乐寺——安乐村小,我曾经住过半年的地方。安乐寺和39年前相比,整体上没有改变,只是更陈旧了。山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门额上结满蛛网,安乐村小四字依稀可见。门前的石梯下长满了杂乱的荒草,旁边的球场也是蓬蒿满地。看样子村小已经废弃了很久。我走到靠左角的窗口下,久久凝视着那片暗黑色的窗板,当年我就是住在这间屋里,那里曾经印下我无数的脚迹。隔壁那间,就是我办政治夜校的地方。岁月匆匆,斗转星移,故地重游,我已经从当年的青年变成了花甲老人,能不感慨系之。
由于大门紧锁,我无法到里面去凭吊,但心里已经满足了。
走过安乐寺就进入了吴家场。昔日的吴家场已经面目全非,狭窄的石板路,路旁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杨国旺的中医诊所,黄仲荣的代销店,黄仲华黄仲贵刘纯芳等的房子都已经无影无踪。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拆掉,或变成新的砖房,或残存一片废墟,只有当年刘松云的土墙屋还原封不动,但是也挂着大铁锁,人去屋空。我在刘松云的老屋旁认出,那片乱草丛生的荒地,就是姚毛儿“遗址”,不禁又想起这位奇人。
打米房前那颗黄葛树还在,比以前更茂盛了,蟠曲苍劲的树干撑起一片绿荫。多少年来,也许只有这棵黄葛树一直在这里默默地注视着发生在吴家场上的一切。
走过黄葛树,几十米长的吴家场就结束了。前方的树荫下却有一座两层的砖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一个光着上身的老人慌忙迎出来。一问,原来是刘光成,已经年近八十了。刘光成就是刘松云的儿子,刘哑巴的哥哥。我向刘光成做了自我介绍,他睁大眼睛把我看了又看,说:“哦……哦……”
刘光成说,他父亲刘松云活了97岁,已经去世,弟弟刘哑巴晚年住进拔山养老院,去年也去世了。他听说我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还没有忘记他们,一定要留我们吃饭。我们婉谢了。我和刘光成聊了一会,眼前浮现出他当年身强力壮的某些断续画面,他此时的模样,很像刘松云当年的样子,眼中也有些模模糊糊的。
我问刘光成,当年的队长向志雪在哪里。他说就在安乐寺前面新修了砖房。于是我们又原路走过吴家场,到了向志雪家里。向志雪已经很苍老了,我仔细辨认,还是从他面部看出了当年的模样,眼睛鼻子基本没变。面对我这个不速之客,他有几分惊讶,当知道我是谁后,顿时张大了嘴巴。“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到这里当过副队长,我是队长。呃呃,是的是的……你是陈队长。”他老婆正蹲在地上“麻”包谷(从包谷棒棒上把包谷颗粒搓下来),抬头看我,我也依稀辨认出了她。
“我75岁了”,当年只有36岁的向志雪说。
我想起了“云崽”,就问“云崽呢?”
“哦,云崽,他叫向天云,在浙江打工。”
向志雪的房子四间两进两楼,很宽敞,比起当年,有天壤之悬。
我和向志雪回忆起当年的事情,他竟然还记得我带头挖旱田的事:“那块田还在,那天我也在一起挖。”当时我带领社员们大挖旱田,一天超过三天的面积,我的双手全是血泡。
向志雪不知怎么一会儿就把热气腾腾的荷包蛋端到我们面前了,还提出几瓶冰冻雪花啤酒来招待我们——家里当然有冰箱了。这一瞬间我不禁回忆起当年在他家吃饭时的那种困窘场面,这几十年变化真大呀。
我依次问起当年的社员们,向志雪告诉我,大部分都搬走了,还有一部分外出打工多年未归,现在留下的人不多。我问起姚青灿,也就是姚毛儿的弟弟。他说,就住在旁边。我立即请他带路去寻访姚青灿。
姚青灿的房子比向志雪的还大得多,两层楼的砖房,长长的一排,我都没来得及数出有多少间。还未进屋,我就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当年姚青灿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床上,穷得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现在怎么就这么富裕了,可见,只要不瞎指挥,每个农民都能够靠勤劳过上好日子。
跨进姚青灿家,他老婆王宗兰热情招呼我们坐。王宗兰已经70多岁,苍老得很,可是比起当年,却多了几分尊严。我不禁暗暗想起当年她拿扫帚疙瘩痛打姚毛儿的事情,真的是恍如隔世啊。姚青灿在隔壁床上躺着,身体欠佳。我走到床前问他还记得我吗,可惜他耳朵听不到,无法交流。
姚青灿的女儿站在一旁,就是那个当年还在王宗兰背上揹着的女孩,已经四十了,她不记得我。当然啰,那时她才一岁。遗憾的是,这个女儿右手从手腕以下完全没有了,她告诉我,是在广东打工时被机器轧去的。闻之不胜悲哀。沿海的经济发展,是用无数农民工的血汗乃至肢体换来的。
说不完的话,回忆不完的往事,因为我不忍心让罗老板耽误过多时间——虽然他一再表示无所谓,我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吴家场。我站在安乐寺的台地上环顾四周,当年那些光秃秃的山包全部都变得一片葱茏,没有了人为的破坏,草木自然会蓬勃生长。我不禁又感慨,当年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去和大自然过不去呢?
我登上汽车,挥手向前来送我的老乡们告别,安乐寺转眼就从眼前消失了,就像梦幻一般。
第十二章 铁竹木棕
【1】同时兼管两个门市部
1975年夏,我结束了在吴家场的工作。早先发给的《劳动手册》我都如实登记了,劳动出勤基本合符要求。我老老实实把《劳动手册》带回公社准备接受考核,却根本没有人管这件事。原来半年前说的话已经没有人记得了。除了我,没有一个人带回《劳动手册》。后来我慢慢明白,很多事情都是说空话,起先说得热闹非凡,后来就不再提起,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会当回事。只许诺,不兑现,有始无终,而且从来无人追究,这也是中国特色吧。
显周公社的干部在两年间有了一些变动。公社书记李占芳调走,以前曾经在显周任过书记,后来调到县农业局去的陈德金又调回了显周。据说李书记干工作没有魄力,陈德金却是极有魄力之人,目前大搞农业学大寨,需要陈德金这样的人。陈德金是八德公社白土大队人,农民出身,十足的文盲,只能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其人满脸大麻子,有一只眼睛还是“玻璃花”,人们当面喊陈书记,背后却喊陈麻子。陈德金所谓的魄力就是讲蛮干,他是一把做农话的好手,任何农话都难不倒他;他是实干家,到队上检查工作,为了示范,可以马上挽起裤脚跳到水田里犁田栽秧,也以立即扛起杠子抬石头。
显周供销社人员也有变动,生产门市部的许世堤早已调到拔山任生产资料经理,接替他的是八德人胡德学,外号“二保长”,由庙垭供销社调来。胡德学来了不久也调走了,新来了一个副经理何正虎任生产门市部营业员。何正虎不到30岁,是转业军人,军人气质,双目有神,练达精干,为人耿直豪爽,业务能力强。因为都是拔山供销社的年轻人,我以前就认识他,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显周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何正虎和我成了朋友,很快也就和猫儿以及一群知青成了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高谈阔论,当然,也说怪话,吹黄段子。他虽然是我的领导,但是却像兄弟一样相处。我的交友之道从那时就定型了,只要成了朋友,就不再是领导。如果仍然是领导的架子,那就不是朋友。这种态度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在朋友之间,我从来不耐烦叫官衔,都是直呼其名,或者称兄道弟。
那年忠县要修建川汉输气管道公路,要从各部门抽调人员参加会战,何正虎被选中了,必须立即到岗,官员们竟然决定我接替他的生产门市部营业员。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人生又改变了坐标。
我很害怕当营业员,搞“三分之一”时沈昌荣说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小陈,你最好想办法离开供销社,免得以后搞运动走不脱。”他说的就是不能当营业员。同时,我对生产门市部里各种农药的毒气也心怀恐惧,到显周的第一天闻到那股刺鼻的农药味就难受。没有想到,仅仅在两年后,我就要成为生产门市部的营业员了。我知道在社会主义中国自己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每个人都是革命螺丝钉,别人把你拧到哪里就是哪里。除了立即应命,无任何条件可讲。
何正虎悄悄对我说:“也好,生产门市部是有毒工种,每月可以享受一斤白糖一斤猪肉的营养补贴。”一斤白糖一斤猪肉加起来值不到两元钱,且不说钱多钱少,这点补贴真能抵消农药对身体的毒害吗?
9月1日到3日,通过盘底,何正虎把生产门市部正式交给了我,从此,我每天都必须站在充满毒气的柜台里当售货员了。更恼火的是,韩家虎由于某种工作需要也要交出食品门市部,潘经理竟然把食品门市部的业务也交给了我。这样一来,我就同时兼管两个门市部的业务了。
【2】我直接服务农业
在年复一年近乎狂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作为农业后勤的供销社打出了“后勤变先行”的旗帜。商业开始高度政治化,不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围绕农业办供销,办好供销为农业”是当时整天高喊的口号。口号归口号,落实归落实,真正直接服务农业的,就是生产门市部——其全称是——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生产门市部以出售农业生产资料为主,也兼营少量日杂用品。生产资料分为“铁、竹、木、棕四大类。铁包括锄头、铁锤、錾子、耙梳、犁铧、钉子等;竹包括纤索、围席、斗笠、箩筐等;木包括风车、撘斗、锄把、杠子、犁头等;棕包括蓑衣、棕绳等。除了这些传统的生产资料,还有化肥、农药,水泥等。生产门市部的商品大都较笨重而且体型较大,不适合摆放柜台,都全部散放在室内任人挑选,有点像现在的超市。200多平米的门市里,分类排列着各类农具,到了赶场的日子,农民们拥挤在里面选购物品,选好后到柜台前来交钱。如果是锄头,还得称秤,按照重量计费。柜台上常年备有一个小碗,里面用水泡着土红颜料,搁着一只粗大的毛笔。交了钱,就在物品上抹一个红记,表示可以离开了。
由于货物散放,就要随时防备有人行窃,所以,每到赶场时,就会请一个代销员来帮忙,每天一元钱工资。经常来的代销员是天堡大队代销店的刘廷志,30多岁,劳力很强,办事也还能干。
门市部的大概布局是,进门的右边是侧面靠壁的一排货架,摆放着农药223乳剂、乐果乳剂、亚胺硫磷乳剂等农药,喷雾器的喷嘴、接头等配件,鞭炮、菜刀、合页、拉手、钉子等日杂用品。与货架平行的是长长的柜台,柜台至少二十年了,没有一点油漆,粗糙的木纹已经磨得发亮。一把木秤一把算盘搁在柜台上,都是上了年龄的东西,陈旧不堪。
进门的左边是专门堆放化肥的,地下被长年渗透出的化肥浸润得湿漉漉的。那时最好的化肥是尿素,因为形似蚂蚁产的卵,农民称之为蚂蚁蛋。尿素每袋80斤,每斤0.225,每袋18元。因为物资紧缺,尿素肥是按计划供应,精确到个位,不得多出一斤。除了尿素,更多的是碳酸氢铵和过磷酸钙,比较廉价一些。靠近化肥是堆放竹箩的地方,竹箩分为过箩和挑箩,前者是量具(过就是衡量之意,就像称秤又叫过秤一样),后者是工具,用来挑粮食。忠县后乡搬运粮食不用揹,都用挑,挑箩家家都有,用量很大。
门市中间是铁器,锄头用一个大架子整齐地挂成上下三排。木柱子上挂着长长的水牛犁田用的铁纤索,传统的竹纤索已经慢慢淡出。铁纤索就是铁链,手工打制,一碰就发出清脆的哗哗声。一大堆锄把扁担犁头等挨放着。再往里是“六六六粉”,杀虫用的,毒气很大。靠最里就是宽大的撘斗,每个大约有三平米,几个叠在一起,顶到楼板。
我每天就在货架和柜台之间站着称秤抹红收钱,到了晚上就把当天收的钱存到对面的信用社去。
整个门市部永远弥漫着熏人的各种农药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有时会让人睁不开眼。我知道无法摆脱,只有认命。
【3】氨水池旁惊魂一幕
农用物资的奇缺,对于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个难题,要想提高产量,而化肥远远不够,于是氨水便应运而生。
氨水用大量的清水稀释后可以作化肥用。由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生产的氨水用木船运到忠县码头,再用汽车转运到各个公社,由生产门市部出售。每个公社都为此专门修建了氨水池,在靠近公路的地方用石头砌成一个六面体,里面用水泥抹得严严实实。池子底下安一个水龙头,用来排放氨水。每当氨水运到后,公社就通知各队依次来挑氨水,一队队的人挑着氨水上路,很壮观。
氨水有一个特点,就是毒气熏天,人离得近一点会无法呼吸睁不开眼睛。挑氨水的人都纷纷叫苦。只要有挑氨水的队伍经过,老远就是刺鼻的毒气。挑氨水的粪桶放过的地方,杂草会全部死掉,现出一个干枯的圆圈。氨水队伍倘是停下歇气的时间长了,路边的麦苗都会枯死。最痛苦的不是挑氨水的人,他们只是临时性的,最痛苦的是卖氨水的人,必须一直坚守在池子旁,一桶一桶地卖,不得擅离。显周公社的氨水池建在粮库旁的公路边,为便于汽车卸载,池子建在地下,只露出地面少许。挑氨水的人要通过地道般的石梯才能走进那只水龙头。浓浓的毒气在地道里无法散去,越积越多,形成一个毒气室。卖氨水的人实在受不了,就飞跑出来换一口气,再返回工作。
我就是卖氨水的人,那个滋味之难受,无法用言语表述。还好,帮我看门的刘廷志分担了很大一部分。
池子里的氨水卖完后,会有汽车接着运来。每当有运氨水的汽车到来,我作为实物负责人,都到现场去收货。氨水装在一个硕大的胶囊里,把胶囊尾部的管子接到氨水池的注入口,满车氨水就哗哗地流到池子里。这时的毒气也熏得够呛。
大概在1976年的暮春,在氨水池旁发生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
那天,忠县汽车队的司机赵继华开着一辆载重汽车,给显周运来了八吨氨水。氨水在圆滚滚的胶囊里波动着,胶囊一阵阵地颤动。我在氨水池旁边指挥赵继华倒车,一连到了几次,胶囊尾部都没有对准池子的注入口。那是一条大约20度坡度的坑坑洼洼的碎石公路,赵继华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方向盘,在公路上挪来挪去找位置。忽然汽车在坎坷的公路上重重地弹了一下,整个车厢剧烈地颠簸着,躺在车厢里的胶囊顺势滚动,越过后厢板凌空跌落下来,砰的一声,轰然爆裂。
忽然发生的事情令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就在一瞬间,氨水像山洪暴发般倾泻而出,形成一尺多高的波涛。一股巨大的气浪劈头压下,仿佛有山一般的重量,我头部像被重物猛的击打了一下,差点站不稳。毒气形成的气浪虽然看不见,却明显压迫着我,一时眼泪和鼻涕交流,好像世界某日到来了。我来不及多想,拔腿就跑。汹涌而来的氨水在我身后追着我,毒气一阵紧似一阵地压过来,我感到快要窒息了。
一部分氨水流进公路旁边的排水沟,腾起阵阵黄色的浪花。毒气所至,路边一排排高大树木上的绿叶立即干枯,水沟里的野草立即干枯。哗哗哗的氨水一直流到公路尽头,又顺势流下山坡,消失在去显周场的路上。所经之地,草木在几秒钟内全部干枯,就像被大火烧焦了一般。
粮库里的工作人员和山坡上的农民们都被惊呆了,捂着鼻子茫然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一口气跑到粮库的晒坝里,这里地势较高。这时八吨氨水已经无影无踪,那个被摔破的胶囊瘪瘪地躺在公路边一动不动。赵继华刚才见势不妙,下车往坡上跑去了,他和我方向相反,因为出事时他和我分别在胶囊的上下两边,氨水是往我那边奔流的。此时他惊魂未定,呆呆地看着破胶囊,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人们好像如梦初醒,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
“好吓人啰!”
“狗日的,把树叶都烧卷了。”
“你看,草都没得了。”
“幸好老陈跑得快哟。”
毒气已经飘散了许多,现场不再恐怖。这时我却紧张起来,八吨氨水就这样流失了,我是实物负责人,这笔经济损失谁来承担?要是记到我头上,我赔得起吗?
我马上写了一份现场记录,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请赵继华签字盖手印。又请在场的目击者十多人,包括粮库会计陈之高、粮库搬运刘廷玉、杨世艳、袁世福等都签字盖手印为我作证。
后来拔山供销社将此次损失的八吨氨水全部报销。
氨水流过的水沟一年内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想起那惊魂一幕。
【3】遭遇昔日“孤胆英雄”
生产门市的商品有一部份是靠自己组织收购再出售,比如锄头镰刀粪桶鞭炮等,一些制作这些产品的匠人便经常上门来向我推销。
这一天,一个中年农民走进了我的门市,在里面慢悠悠转了一圈后,来到柜台前叫了声:“陈同志,忙啊。”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随口应了一声。一支烟从那人手里轻轻丢到了柜台上,“抽支烟吧。”我素来不抽烟,就婉谢了。这时我不由得认真打量了一番来人,只见他头戴一顶皱巴巴的灰蓝灰蓝的干部帽,帽檐向下耷拉着,身穿着同样皱巴巴的灰蓝灰蓝的中山服,扣子已经掉了一颗,肩头是用很稀疏的针路打上的补丁。那顶干部帽虽然破旧,却显示着他和一般农民的区别,山里的农民都是包帕子,很少有戴帽子的。再看他的神态,就更与农民不同了,他一支手插进裤袋里,一支手夹着烟,眼神镇静而从容,淡淡的笑容中透出几分狡黠来。
他叫陈百新,新立公社华严大队人,来找我的目的很明确,他在生产鞭炮木桶,想和我建立产销关系。我看他很能干,产品质量也可以,而且我也正好需要,就答应了他。此后,陈百新多次到我的门市来交货,我们彼此就很熟识了。
有一天,一个老人对我说:“陈百新这个人不简单啰,很有计谋呢。他以前是精华信用社的主任,是因为出了事才回家务农的。”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蓦地闪回10年前的一段记忆。
10年前,上山下乡到精华公社的姐姐陈琳曾经讲过一段故事。精华信用社主任某人在“四清”运动时因为自编自演“孤胆英雄”的故事,事情败露后被开除回家。当时我还在上小学,但是印象极深。难道眼前这个陈百新就是那个“孤胆英雄”。
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我小时听到的故事中的人物此时和我相遇了。
陈百新的故事发生在1965年冬天。那年,“四清”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据档案记载,在运动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县就有97个人自杀身亡。一县如此,全国有多少冤魂可想而知。在一些人含冤死去的同时,却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积极分子。从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宣传英雄人物和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的文章,“英雄辈出”四个字频频出现,大约那个时代每年产生的英雄比以前100年的总和还要多,积极分子们争当英雄已经蔚然成风。就在这种背景下,陈百新出现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精华山已经飘起了小雪,远远近近的山岭都笼罩在一片萧飒中。在精华公社信用社做主任的陈百新下乡收了一天的贷款后,已经暮色苍茫了。那里离公社还很远,至少十多里吧。他将收回的现金装进一个袋子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就匆匆往回赶。才走到半路上,天就黑尽了。
就在这时,他借着淡淡的月光发现在他身后远远地跟着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这一刻,他想起了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深更半夜的,一定是阶级敌人盯着我身上的公款追来了。正在考虑这些时,那几个人影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他焦急万分,自己被害是小事,可是公款是大事啊,无论怎么都不能让国家财产落入阶级敌人之手。急中生智,他加快步伐跑过一个山头,趁几个人影隔在山头那边,迅速地将装钱的塑料袋子塞进路边的水田里,然后在田坎上按了一个手印作为记号。当他做完这一切后,几个人影已经越过山头追了过来。果然是几个凶狠的阶级敌人,他们上来就要陈百新把钱交出来,不然就要他的命。陈百新机智地和阶级敌人周旋,不让阶级敌人的阴谋得逞。阶级敌人扑上来凶狠把他按在麦地上,他拼命挣扎,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从麦地的这一边一直滚到另一边。敌人搜遍他的全身也没有找到一分钱,一怒之下将他捆起来扔在麦地里扬长而去。
第二天清晨,人们在麦地里发现了已经冻得全身发紫的陈百新,当人们忙着去解开他的绳索时,陈百新哆嗦着说:“钱……钱……钱在……水田里。”人们根据他的指点,果然在田里摸出了那个装着钱的塑料袋子,这时陈百新已经昏迷过去了。
又一个和阶级敌人英勇搏斗的英雄出现了,陈百新在病床上醒过来后,心里想着的就是迎接鲜花和掌声了。
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开展侦破,为的是尽快抓获那几个可恶的阶级敌人,将阶级斗争推向新高潮。令民警们遗憾的是,阶级敌人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更奇怪的是,连陈百新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麦地里的麦苗竟然没有踏倒一株。民警们头上顿时疑云密布,正准备对英雄人物的宣传便暂时停了下来。
民警们转而对陈百新进行了调查,令所有人惊讶不已的是,所谓的与阶级敌人进行搏斗竟是陈百新自编自演的丑剧。
原来陈百新看到报上不断涌现出那么多的英雄,对那些英雄产生了怀疑,怎么总会有那么多阶级敌人在破坏呢?有一天忽然恍然大悟,那些英雄人物可能都是假的,我自己其实也可以当英雄。我们这里不是也有阶级斗争,也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吗?于是他便精心策划了这场丑剧,他煞费苦心地把钱袋塞进水田,在田坎上按了一个手印,请一个最信得过的兄弟把自己捆起来扔在麦地里。然而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在兴奋之中忘记了把麦地狠狠地践踏一通,制造出搏斗的“现场”,就是这一点失误让他前功尽弃,所有心血统统付之东流。要是当时他把麦地践踏了,情况又会怎样呢?他会成功吗?而另一些功成名就的英雄,和陈百新相比,是否就是在造假上略高一筹而已?
倒霉的陈百新在露出真面目后受到了严厉的惩处,他被开除革命阵营回家当农民,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正是如此,才使我在后来有缘认识了这位奇人。
我应陈百新的一再邀请去他家里做客,进了门才知道他日子过得很艰难,英雄梦破灭后,他声名扫地,狼狈不堪,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在那个精神空前膨胀而又物质空前匮乏的畸形时代,他虽然有精明的头脑也无法摆脱贫困。后来和人合伙做鞭炮之类的,情形才稍好点。在他面前,我绝口不提他当年的“英雄”壮举,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怕触动了他那根痛神经。
1976年,我准备考虑结婚的大事了,陈百新特地送了一口刷着红漆的木箱给我。他认识很多木匠,又主动推荐了两个手艺出众的木匠师傅来给我做家具,而且表示,工价可以很优惠。当时做的那套家具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虽然样式早已过时了,我还舍不得丢,因为质量确实很好。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