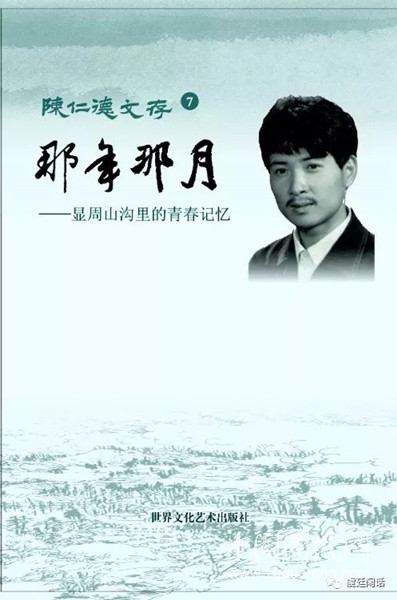
【3】 无法下咽的忆苦饭
“三分之一运动”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都有相对固定的程序,比如发动群众,排队(划分敌我),培养积极分子,忆苦思甜,斗争地主富农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忆苦思甜中的吃忆苦饭。
执政者自称他们把农民从饥寒交迫中解放出来,而且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国都是一片黑暗,人民世世代代受尽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成年累月挣扎在生死线上。当时著名的舞剧《白毛女》插曲的歌词是“上下五千年,受苦又受难”。尤其是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个时代被称为万恶的旧社会,人民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的全是猪狗食。为了让人民牢记共产党的恩情,要经常性地制度化地回忆旧社会的“苦难”,记住新社会的“甜蜜”,这就叫“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是忆苦思甜的重头戏,是那些年反复上演的保留节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法宝之一。具体讲,吃忆苦饭就是仿造出旧社会的猪狗食,大家一起举行宗教般的集会,虔诚地共进猪狗食,从而更加仇恨万恶的旧社会,更加热爱如同天堂般美好的新社会。
沥石大队吃忆苦饭选在6队汪家大湾举行,我作为工作组成员,与组长沈昌荣、大队书记萧朝官等一起参加。
在冬日的薄雾中,来自全大队的约100多个贫下中农陆陆续续来到了汪家大湾,记得是在腊月里,寒风凛冽,大湾里一株樱桃花刚刚开放。我以前以为樱桃花是春天开放,那次才知道樱桃在腊月就迎着寒风开花了,是最早开花的。这一点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回忆起汪家大湾,就会想起在那里见过的樱桃花以及忆苦饭。
参加吃忆苦饭的人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丝毫看不出他们生活的美满,这和忆苦思甜的主题有些相悖。但是,那个年代每天都悖论百出,即使荒谬绝伦,也没有人敢于质疑。
萧朝官宣布大会开始,大家一起五音不全有气无力七零八落地唱忆苦专用歌曲《天上布满星》:“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唱完《天上布满星》,萧朝官和沈昌荣先后讲话,无非是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赞成等等。
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忆苦饭端出来,每人一碗。我也带头端起一碗,和大家一起吃。
这次的忆苦饭是用粗糠和着油菜叶葫豆叶捏成的团子,黄色的谷壳大块大块地混杂其中,团子硬得像石头,用筷子戳不穿。我是工作组的同志,在这种场合是决不可以回避的,我把碗举起来示意大家:吃!然后将一个梆硬的糠团子塞进嘴里。虽然我对忆苦饭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其粗粝仍然超过了我的想象。那个糠团子如同木渣,只咬一下就满口乱钻,卡在嘴里无法下咽。我下意识地想立即吐掉,但环顾左右,却见所有贫下中农都吃得津津有味泰然自若,我岂敢当众吐出,只好假装咀嚼,却暗暗将糠团子含在嘴里,半天没有吞下一点。最后装着巡视会场,到旁边一个角落里迅速将糠团吐出,再若无其事地回到会场,这时贫下中农们已经不徐不疾地把所有糠团吃得精光了。
我不禁十分惊讶,这种连猪狗都不会吃的东西,他们怎么吃得下?吃下又怎么消化?惟一的答案是,他们平常吃的饭菜比起“忆苦饭”一定好不了多少。
【4】精彩的忆苦表演
萧朝官书记接着宣布忆苦报告开始,于是最精彩的节目开始上演。
沥石9队队长刘纯华走到院坝中心,他中等个子,身形干瘦,脸上起伏着一些不知什么原因形成的小疙瘩,脸皮泛着蜡一般的冷色,眼睛斜着,头上盘着一根黑黢黢的帕子,身穿一件已经很破的衣服。他一言不发,冷峻的眼光扫过全场,像是在搜索什么。
时间仿佛缓缓地停顿下来。
“今天的糠粑,你们说,好不好吃?”他忽然大叫一声。
全场都愣住了,没有一个人出声。
“我说就好吃。好吃——得很!”他拖长了声音说。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解放前……我们哪里吃得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糠嘛。解放前我们哪里有糠吃?糠是谷子打出来的,要有谷子才有糠,我们连谷子都没有哇,哪里会有糠呢?”
说到这里,他作痛心疾首状,脑袋摇摆着,用右手的手背使劲击打左手的手心,发出砰砰的声音。
“解放前,我们都是吃猪狗食,吃野菜草根,哪里吃得到糠。伤心啊,我刘纯华解放前受苦受难,没有住处,搬了27次家。搬了27次家呀……”说到这里他的语调明显低沉下来。
“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刘纯华早就饿死了,今天还会在这里和大家相会吗?”他的精神又振奋起来。
这时他出人意外地解开了他的衣襟,两手大幅度地撩开那件破衣服在石坝里走来走去说:“解放后我的生活好幸福啊。你们看,我穿得多好啊。你们看,你们看。”
他兴犹未尽,还来不及扣好衣服,又呼的一下把头上黑黢黢的帕子扯下来双手捧着说:“解放后,我还包上了帕子。”他将长长的帕子左右抖动,许多陈年的头皮屑纷纷飘落……
我觉得刘纯华真是个天才的演员,能够就地取材,用最简单的道具表达最深刻的主题。其语言的波澜起伏,轻重缓急,均有过人之处。事后得知,他早就身经百战,成了忆苦专业户了。我虽然见过不少忆苦表演,但是像他这样精彩的,还只此一人。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0年,他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一招一式,依然清楚地浮现在我眉睫间。
吃忆苦饭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真应该授予发明专利奖才对。这个发明在中国持续二三十年,直到人人厌恶至极。最后连邓小平都感到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了。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这才给忆苦思甜画上了句号。
【5】 复员军人的故事
汪家大湾有一位叫汪良国的小伙子,年龄和我相仿佛,生得浓眉大眼英气勃勃,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说话还带一点儿普通话腔。汪良国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老贫农,总想把家庭搞好点,让儿子早点娶个媳妇成亲。那正是成天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发家致富是最大的罪恶,我们搞“三分之一”的目的就是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响当当的口号是:“不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谁敢把家庭搞好?汪良国就经常批评他父亲,教育父亲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一次,我和沈昌荣都在场,听见汪良国又在说他父亲,他父亲忍不住回答:“我就是这个资产主义思想”。老人成天听“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两者搅合成了“资产主义”。汪良国急了,说:“爸爸,你这样不行,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老父亲说:“饭都吃不起,媳妇都讨不到,啥子道路哦。”
我在一旁觉得好笑,却不敢笑。那时不要说中国的农民,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在完全封闭的环境里,都没有见过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模样,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从宣传资料上来,可惜编写宣传资料的人也从没有一个人见过资本主义,就这样几亿人异口同声稀里糊涂地把从没见过的资本主义臭骂了几十年。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离资本主义还相差甚远,却要快速奔向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其结果就是像刘纯华这样的人,一副极度营养不良的身躯,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却装模做样地在那里一次次地忆苦思甜。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而岁月已经流失了30年,无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人已经在浑浑噩噩中死去了。
有次我偶然谈起毛泽东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粕”字在忠县方言里是读“伯”,与普通话读音不同。汪良国听到我发音后立即纠正我,说“粕”字应该读“PO”,我说我是用的方言,不能满口方言,单独一个“粕”字却读普通话。他回头去柜子里搜出一本小学生字典,翻开指着粕字给我看,应该读“PO”。这小伙子是个很认真的人。
沈昌荣也在一旁,他是个老复员军人,当然熟知这些,随后他给我讲了一个青年农民当兵复员回家讲普通话的故事。
拔山区八德公社有一个青年农民去部队混了两年后复员回家,居然记不得老家的小路。走在山坡上,看见有一个老农民在犁田,就走过去用怪怪的普通话腔调问:“喂,前面那个老头,到周家湾怎么走?”那个老头听不懂这种腔调,就回过头问:“说啥子哦?”这时青年人才发现,这个老头就是自己两年不见的父亲。父亲见到儿子好不高兴,立即收拾停当,带着儿子回家。谁知儿子一路还是用怪怪的普通话腔调和他说话,让父亲很不高兴。到了家门前,儿子看见有个一岁的孩子趴在门槛上,就问:“这是谁家的小子啊?”父亲笑着说:“你走后家里又添了个弟弟,他是你弟弟呢。”儿子闻言将父亲看了又看,依然用怪怪的腔调说:“你这么老了,还干这玩意儿?”父亲这次听懂了,气得抡起巴掌掴了儿子一耳光。
我听到这个故事不由得开怀大笑。
沈昌荣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就发生在他老家附近。
【6】非团员负责发展新团员
历次运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党团员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三分之一”运动也一样。
沈昌荣和我商量,由他负责发展党员,由我负责发展团员。我一听大吃一惊,我自己都不是团员更非党员,怎么有资格负责发展团员,于是当即向沈昌荣表明,我从没有写过入团申请书,至今还不是共青团员,不能承担这一工作。
沈昌荣笑了笑说:“小陈,你不是以个人名义负责,而是以工作组名义负责,没问题的。这些我知道。团组织不像党组织那样严格,要宽一些,你大胆干就是。”
我听了沈昌荣的话,没有退路,既然是以工作组的名义,那就干吧。
随即根据大队萧朝官书记推荐,物色了十来个出身贫下中农的青年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写入团申请书,主动向团组织靠拢。没有几天,我就收到了十多份入团申请书。那时入团申请书是要交代祖宗三代的,我在仔细审看时发现一个青年的申请书上写着“爷爷陈仁德”。陈仁德不是我的名字吗!他爷爷也叫陈仁德?我把那个青年叫来,先绕着弯子问他对入团的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什么的。最后才问:“你爷爷是陈仁德吗?”那青年仰起头来,露出腼腆的笑容,轻轻地说:“是的,我爷爷是陈仁德。”然后他反问,“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没什么没什么。你可以走了。”那青年只知道我是陈同志(那时习惯把国家工作人员叫某同志),不知道我也叫陈仁德。
那青年离开后,我捂着嘴笑了。
汤玉辉也写了入团申请书,里面交代她的父亲解放前在重庆经一个叫“华四软”的国民党员介绍,当过什么部门的稽查,解放后定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云云。
我把所有申请书交给沈昌荣审核,他一边说“小陈看了就是了”,一边就认真审核起来。看完后说:“这些都可以吸收入团。叫他们填志愿书吧。”我特别提出汤玉辉的出身问题,他说:“没关系,可以入团。她在生产队表现很好,大家都夸奖她。”
我就把《入团志愿书》发下去,没几天他们就全部填好交了上来,我就在每份《入团志愿书》签注意见,一律是“同意入团。沥石工作组。X年X月X日。”这样,我这个并非党非团的人主持了一次发展团员的工作。
事后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团员身份好些,第二年,请公社团委书记胡兴秀当我的介绍人,“光荣”加入了共青团。
发展党员的工作我没有负责,但是也参加了。在大队支部会上沈昌荣说:“今天的支部会是扩大的支部会,因为小陈参加了。”印象最深的是,插队沥石1队的重庆知青蒋树平被沈昌荣看中了,多次找蒋树平谈话。蒋树平受宠若惊,立马向沈昌荣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 蒋树平生得白净斯文,五官端正,胖乎乎的脸蛋,很有亲和力。没多久蒋树平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可能是那时全公社惟一加入共产党的知青。入党后,蒋树平处处展露头角,成为小范围内的政治明星,在不久后的一次征兵中,他又“光荣”入伍,从此离开了农村,据说去了沈阳军区某部。他视沈昌荣为恩人,后来长期保持联系。
【7】深山洞穴探寻夜明砂
我虽然在沥石大队搞“三分之一”,但我还是供销社的人,在供销社领工资,只要供销社有特别紧要的任务一时人手不够,我也应该参与。那时每年到了秋后都要大张旗鼓地搞“小秋收”。之所以叫小秋收,是为了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秋收。传统秋收是收获粮食作物,小秋收则是收获粮食作物之外的副产品和手工产品废品野生品等,如野生油料、野生纤维、野生淀粉、野生化工原料、野生药材,以及其他可以利用的野生动植物。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小秋收显得很重要,所以那年权威的《人民日报》特地发表了文章《认真搞好小秋收》。《人民日报》文章几乎相当于中央文件的威力,只要《人民日报》文章说重要,那就得赶紧当成政治任务去做。
县里给各区下达了小秋收的收购计划,区里又下到各公社。具体是多少我记不得了,反正任务很重。这下潘经理急了,好在他有着应对各种任务的丰富经验。他召集供销社职工开会,把供销社代管的综合食店两位老人也通知来参加。说到可以大量收购野生药材,综合食店年近70的老大爷潘正堂说,他家附近有一个山洞,洞里千百年来蝙蝠成群,蝙蝠排泄的粪便就是药材,名叫夜明砂。只要敢钻进洞去,保证能找到夜明砂。潘经理叫了一声“好”,就在心里打定主意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我是显周供销社最年轻的职工,我不去,谁去。
我从沥石大队回到显周场,潘经理把任务交给了我。我立即表态,坚决完成任务。从知青时代起,吃苦还少了吗,这又算什么。我不仅表示了积极的态度,而且在内心深处,还真有那么一点向往,想去探究一下那个神秘的山洞。
初冬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我穿上那件多久不穿的蓝布对襟衣,挑着一对箩筐,与潘经理和潘正堂老人一起上路了。
潘正堂老人家住花桥公社英明大队,离显周场十多里山路。我挑着担子悠闲地跟在他们后面,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潘正堂老人家里。潘正堂老人吩咐他老伴做饭,先招待了我们,再带我们去找那个山洞。
在一片莽莽苍苍草木稀疏人迹罕至的山岗上,潘正堂老人找到了那个山洞。
这是一座石山,整座山都是坚硬的青石,在靠近地面的位置,有一条高约一尺宽约四尺的石罅,像是石山裂开的一个横向口子,往里看黑沉沉不见底。潘正堂老人说,就是这个洞子。
这对我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哪里钻过这样的洞。但是说实话,我一点都没有害怕,反而想一探究竟。年轻时谁都有探险意识,不怕冒险。
我把随身带来的手电筒揣在衣袋里,就试着往洞里钻。头伸进去看了看,发现洞口是一个坎,于是退出来,扑在地上倒着身子先把双脚伸进去,慢慢往下滑,只约四尺高就到底了。这时借助外面透进的光线,可以看见一个大约一丈见方的洞厅,地上很干燥。往前看,又是一个和外面洞口相似的石罅,这应该是第二道洞口了。我回头叫潘经理把两个箩筐扔进来,我提着箩筐又从第二道洞口小心翼翼钻进去。进去后光线越来越微弱,手电筒的光线在暗洞里显得非常昏暗,过一会慢慢睁大了眼睛,才看见洞里很空旷,往里黑沉沉看不到尽头。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我果然看到了一大堆蝙蝠的粪便,我从来没有见过蝙蝠的粪便,但是我看那样子和老鼠屎差不多,就断定是了。我向洞外大声喊:“找到了,有檐老鼠屎!”(因蝙蝠大多栖息在屋檐下,状如老鼠,故忠县方言把蝙蝠叫檐老鼠。)我听到潘经理在外面发出的笑声,“老陈,小心点哟。”他在叮嘱我。
这一堆蝙蝠粪便有一尺多高,像山丘一样隆起。
我继续往左右观察,这里不像外面洞厅那样干燥,洞壁有水渗出,湿润的地上有着十分清晰的花瓣一样的野兽脚印,还有一团团的野兽粪便。毫无疑问,洞子里有野兽。忽然一道黑影从洞子深处飞出,呼的一下从我头顶掠过,吓了我一惊。一会儿黑影又呼的一下飞了回来。我看清楚了,是一只黑色的蝙蝠。显然,我的到访打破了洞子里的宁静,蝙蝠被惊动了。一会儿,便有一大群蝙蝠来回飞舞,听的见它们的翅膀翻飞发出的噗噗声。
我想我得尽快完成任务离开这里,就赶紧行动。把手伸进夜明砂堆里,感觉很干燥,也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堆积起这么多,至少几十年吧。由于时间久远,已经没有什么臭味了。我想我们的祖先也真够风雅,明明是粪便,却叫了这么优雅的名字——夜明砂。我把箩筐半偏在地上,双手并用,把夜明砂往箩筐里扒,最后剩下的就一捧捧地捧进箩筐,正好装满两筐,就又从原路艰难地把箩筐拖出去。潘经理在洞口往上拉,顺利出洞。
我使劲爬出洞口,头上身上沾满了夜明砂和洞中的泥土,脱下衣服拍打一阵,感觉稍清爽了些。潘经理忙着捧起夜明砂仔细查看,潘正堂老人也眯着眼睛看,说;“是的,是的。这就是夜明砂。”
回过头看看洞口,石崖上竟然有前人的题刻,是一首七言诗,“坤与一泒绕山川,土石成山理自然。□□□□□□□,题留千古后人看。”不知是哪个朝代的人留下的,诗很差,第三句现在想不起了。
第二天拔山区就发出了小秋收简报,称显周供销分社找到了80斤夜明砂。
收购门市部的伯有训看了我们辛辛苦苦找回的夜明砂,说泥沙杂质太多了,没有药用价值,不予收购。后来那些夜明砂当成垃圾倒掉了。深山洞穴探寻夜明砂毫无意义,但是却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使我真真实实地有过一次探险。现在回想起来也够冒险的,要是洞里的野兽袭击我,怎么办?
【8】一斤糖精与物资交流会
副食门市的胡秀官和我关系较好,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他拒绝给杜文书打酒,虽然被简报表扬,但是从此和公社的关系却难以修复。大约在11月,他被调离显周,到拔山供销分社苏家副食门市去了。临走时,我和许世堤一起送他。我提着他那个当时最常见的网眼铁壳热水瓶,送他走过显周小学,走过前进1队的一片竹林。他忽然回过头来愣着,望着我和许世堤不说话,眼中流出两行泪来。我说:“秀官,走啊。”他把热水瓶从我手中一下拿过去,流着泪说:“你们回去吧,不送了。”就哭着走了,头也不回。
我没想到胡秀官还是这么重情的人。后来我还到苏家去看过胡秀官,还应邀去过他老家金龙公社千秋(或千丘)大队。他最后因为照顾家庭调回老家,在三汇供销社工作,我也去看过他。
胡秀官走后,接任他的是一个复员军人,家住拔山场上的乔兴富。乔兴富长得很敦实,浓眉大眼,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还保留着一些军人气质。
那正是小秋收搞得起劲的时候,拔山区供销社天天打电话到公社要潘经理回报小秋收进度,本来就有“无事忙”之称的潘经理还真忙起来了。
供销社最喜欢讲的就是以购促销购销两旺,仅仅收还不行,还得促销。促销的重要方式就是开物资交流大会,简称交流会。可是那时物资空前匮乏,拿什么来交流呢?如果完全没有一点紧俏物资,又谈得上什么交流大会?
有了,糖精就是紧俏物资。山民们十年八年吃不到一点儿糖,能够有一点糖精也好啊。拔山区供销社想方设法去外面调拨了几斤糖精回来,每个公社一斤,专门用于开交流会用。每个公社有一万多人口,一斤糖精,每人摊不到一粒,但是一年到头,总有一斤糖精用于供应了。
乔兴富去拔山领回了那一斤珍贵的糖精。当天晚上,潘经理十分神秘地把供销社的几个同事叫到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拿出那一斤糖精,说:“我们一起来分装糖精。”
怎么分装呢?先把糖精用秤精确地分成10等分,当时糖精的价格是每斤28元,每一等分就是一两2.80元。这时就不用秤分了,再说也没有那么小的秤。潘经理把事先裁好的三寸见方的旧报纸一张张铺在柜台上,用一个小调羹凭手感将一两糖精分成28份,每份只有少得可怜的点点儿糖精。这时大家一起动手,将那些三寸见方的旧报纸包成一个个的小包,大约比指头稍大一点儿,那点可怜的糖精在里面沙沙响。
经过大家一起加班,一斤糖精就被包成了280份,每份单价0.10元。显周公社的一万多山民,其中会有280人成为幸运的购买者,从而尝到难得的甜味。280份糖精以副食门市为主销售,另外的门市也分别掌握了一些,以便为副食门市分担压力。
第二天,供销社有糖精的大好消息就不胫而走,传遍公社的山山水水。山民们迅速传递着这一喜讯。这其实是我们有意在宣传,好为即将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造舆论,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来赶场。
举行交流会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山民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小小的显周场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焦灼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虽然是冬日,却满街热气腾腾像过节一样。这时只听一声长长的尖利的哨音:滴滴滴……大家一起仰头看去,却是潘经理在街头衔着一个裁判哨子猛吹。潘经理见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过来了,就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广大社员同志们,卖糖精开始了,几个门市部都有……”话刚说完,人们就涌向了门市部,只见手臂像森林一样伸出来。
“一角钱一包,不要挤!不要挤!”潘经理的声音里流露着几分得意。
一会儿,一斤糖精就被哄抢一空。
“明年还有,明年还有。”潘经理的声调已经低了许多。
第八章 假肉票案
【1】发现假肉票
严冬到来了。显周的冬天很冷,山野萧疏,寒风凛冽,水田里结起了凌冰,那些调皮的小孩小心地把凌冰揭起来,就像光滑透明的玻板。山区里的男女老少都有烤烘笼(当地叫灰笼)的习惯,寒冷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手提一个烘笼。烘笼是用山上特有的白夹竹编制的,竹编艺人把白夹竹划成很细小均匀的篾丝,精心地编织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烘笼。烘笼里面装着一个瓦钵,盛上红红的炭灰(当地叫窑灰),就可以用来取暖了。早上在上学的路上,络绎不绝的小学生都双手抄在一起,把烘笼提在正中,有少数粗心的孩子往往让土钵里的炭灰把衣袖点燃了……到处都是提着烘笼的人,这是当地冬日里的一大风景。
12月的一天,正是寒气逼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我终生难忘的事情。
显周公社接到拔山区电话,称在拔山发现了伪造的肉票,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造假人可能在显周,拔山区供销社决定派出莫夫生和陈守清两名干部急赴显周公社侦破此案,并指令我协助莫陈二人。
拔山区区属单位使用的肉票是由供销社所属的拔山食品站自行印制的。那是一种用老式打字机打出蜡纸、再在油印机上用有光纸印制的票证。每张约有火柴盒大小,上面印着“拔山食品站肉票X斤”,票证下方盖着一枚长方形小红印章,印着“XX月”,表示在当月有效。
就在前一天,拔山食品站在清点当天收到的肉款和肉票时忽然发现有两张面额10斤的肉票有伪造之嫌。经回忆,当天持该票来买肉的是一个青年农民,众所周知,农民是从不享受肉票的,这个农民的20斤肉票是从哪里来的呢?
食品站会计张会灼觉得有些蹊跷,戴上老花镜将肉票仔细地看了又看,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马上将情况报告了区供销社。区供销社领导迅速赶到,大家共同鉴定,确认是假票无疑。
很快就从卖肉的发票存根中查到了那个青年农民的姓名,也搞清楚了他的住地。他叫王用隆,家住显周公社老龙四队——小地名叫老龙嘴。
【2】审问韩祥生
接电话不久,莫夫生和陈守清就到达显周,他们和我见面后,简单介绍了案情,说此案已经被区里定性为严重的经济犯罪,必须迅速破案。
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公社杜文书立即通知王用隆来接受调查。王用隆很快就从老龙四队赶到了公社,得知我们的意图后他很坦然地说,一年到头吃不到肉,快过年了,只好高价买20斤肉票来买肉过年。问他肉票是在哪里买的,他说是以三角钱一斤的价格从仁和七队韩祥生手里买来的。
听到韩祥生的名字,公社就感觉情况比较复杂。韩祥生曾经是忠县三汇区一所中心小学的校长,在“四清”运动中被打成坏分子撤销校长职务,开除回家管制劳动直到如今;其妻莫管静是地主分子,也被管制着。
一会儿,韩祥生便被传唤到了公社——一个穿着灰白中山服,戴着蓝布帽,双手提着 “烘笼”, 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卑微的笑容的中年男人。
韩祥生被带进公社楼上的小屋里,他大概察觉出了什么,脸色变得很紧张,但仍僵硬地笑着。
问了多半天肉票的事,韩祥生都装糊涂,说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莫夫生只好把王用隆叫出来,这一下韩祥生便傻了眼,愣着无言以对。
看上去韩祥生的内心极为矛盾,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过了半天才说肉票是他在拔山场上捡的,此外就什么都不承认了。莫夫生急了,喝令他站到一个独凳上,不坦白不让下来。
莫夫生是从军队来的转业干部,在东北某部十多年,曾参与过许多经济案侦破,经验较多。他认为,假肉票不可能是韩祥生捡的,只能是他伪造的,他家里一定有印刷设备,如油印机等。现在的关键是要韩祥生承认自己是伪造者,否则找不到突破口。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又一直到深夜两点,站在独凳上的韩祥生依然一口咬定是捡的。大家不断发起新的攻势,要他坦白自己的罪行交代伪造肉票的细节,谁是同伙,油印机在哪里?
韩祥生总是结结巴巴说不出来,他甚至要来纸笔写下了“肉票如果是我伪造,我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字据。我看了看,他写的字还颇有风骨,不愧当过小学校长。
就这样一直到天亮,大家都倦了,案情没有一点突破。
【3】是韩国伟干的
案情的重大突破发生在早饭后。
刚吃过早饭,一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来到公社门口,口称看望爸爸,这小伙子脸色黑里透红,眼中流露着些许忧伤,头戴一顶灰色的人造革帽子,身穿一件补了许多补丁的蓝色中山服
原来他是韩祥生的儿子韩国伟,见父亲一夜未归放心不下,所以一大早就到公社来,他一点儿也没想到爸爸已经东窗事发。
韩国伟还没见到父亲就被扣了起来,一时找不到地方,莫夫生就将他带进我那间寝室里。意想不到的是,忧心忡忡的韩国伟一走进我寝室,就盯着我墙上的国画《紫藤八哥》不转眼,忘记了他此时的处境。我们叫韩国伟坐下来,向他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他把韩祥生伪造肉票的事全说出来,这个小伙子此时才如梦初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太年轻,显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下精神就垮了,脸色变得煞白。当得知他爸爸将会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时,他犹豫了一会儿,坦然地对我们说:“把爸爸放了吧,肉票是我伪造的。”
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我们立即到韩祥生的房间去,告诉他韩国伟已经招供了,要他认真坦白交待。韩祥生闻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说:“是我害了国伟,他还年轻啊!都怪我啊……”他哭着说,之所以一直不坦白,就是怕害了自己的儿子。眼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滚滚而下,那种痛苦的表情难以言喻。我不禁为之动容。
事情是这样的。
韩祥生当年任小学校长时,把韩国伟带在身边。那时韩国伟还是个几岁的小孩,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他,见他聪明伶俐,就教他写字画画。韩国伟从小就有过人的美术天赋,在图画老师的精心栽培下,画技日益见长,可惜不久韩祥生就被开除回家,韩国伟的命运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下成了狗崽子。但他对美术的兴趣依然不改,十多岁时,他创作的水彩画《黄钦水库展新容》就参加了全县的美术大展并获奖。由于父亲是坏分子母亲是地主分子,他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只好辍学在家务农。今年快过年了,家里还没有一粒米一块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拔山食品站的肉票,就忍痛花钱买回来,照着样子画,结果居然画得一模一样,足以乱真,这样,就有了后来王用隆买肉票的故事。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卖出了几十斤肉票,获利100余元。韩国伟万万没有想到,假肉票这么快就露了馅。
不过,莫夫生并不相信韩国伟的话,他断定韩家暗藏有印刷设备,这么逼真的票不可能是凭手画的。
于是我们押着韩国伟去他家找印刷设备。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