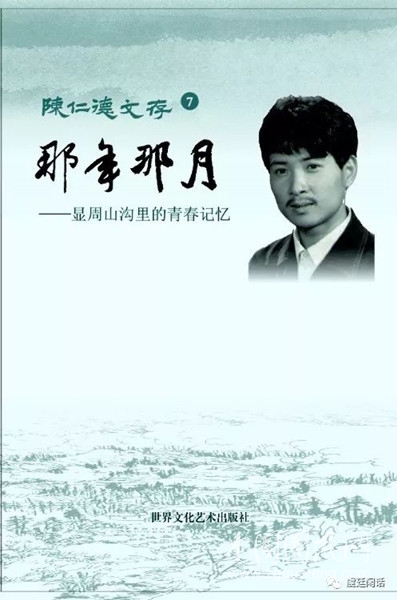
【6】坟上的树已又粗又高
1989年8月,我和杨秀维猫儿重返显周,顺便去给马儿上坟。我们拨开深深的草丛走到坟前,点燃鞭炮祭奠马儿的亡灵。鞭炮飘出的硝烟弥漫在马儿的坟头,久久不散,像是在眷念着什么,我想那就是马儿漂泊在异乡的孤零零的游魂。这时农村早已土地承包了,马儿坟茔所在的土地属于人和一社(生产队改为社了)黄学楷的承包地。黄学楷比我年长20多岁,是一个很厚道的老人,曾经是国军15兵团罗广文部的士兵,后来又转投到解放军队伍中,我在显周期间和我关系很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给马儿上坟时,黄学楷老先生也一起到了坟前,我郑重其事地拜托黄老先生看好马儿的坟,他满口答应。
我们又来到公社旧址前,当年那间差点要了杨秀维命的寝室还在。我们在窗外站立多时,默默地追忆逝去的岁月,追忆那些难忘的场面,秀维特地在窗前留影,说:“我差点在这里被打死了,全靠余部长啊!”
据说马儿是重庆建设厂的子弟,不知道他家中情况如何?世纪之交,我移居重庆,与同为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的李泽全先生交往颇多。李泽全先生在建设厂(今建设集团)工作几十年,退休前曾经长期担任建设厂人事处长,了解那里的许多情况。我迫切地想从他那里打听马儿家庭的情况,可是他却一无所知,这可能是因为建设厂太大了,他无法认识每一个人。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马儿并非建设厂而是空压厂子弟,空压厂我不识一人,无法打听了。
2001年春节,我和杨秀维曾先龙等再次来到马儿坟前凭吊。32年过去了,马儿坟上的树已又粗又高,砌坟的乱石已风化成沙砾,蓬乱的野草在寒风中摇曳着。我们在坟前静静地肃立,谁也没有说话。秀维点燃了鞭炮,劈劈叭叭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山谷里回响,灰蒙蒙的硝烟久久地萦绕在马儿荒凉的坟头。我在坟头再次拜托黄老先生看好坟墓,此时的黄老先生也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2010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黄学楷老先生打来电话,说是由于开发商建房之需,马儿坟即将被毁,他受我之托看照多年,现在已经无力保护了,希望我接到电话后立即想办法。我想,马儿坟虽然不是什么值得保护的东西,但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他死得那么惨,难道三十多年后还要掘墓抛尸,让他再受一次伤害。我立即给杨秀维去电话,我知道不久前一些重庆老知青刚成立了一个知青公会,创办了《知青杂志》,还打电话向我约稿,知青公会不是正好出面管这件事吗。几天后秀维回电话说,知青公会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实力,无法管这些事,没有办法,只有任之了。我不禁仰天长叹。此后马儿坟到底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也无能为力了。
【7】全县爆发了一场围攻知青的运动战
马儿等人被残害时,整个显周乃至整个后乡都发生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知青事件,到处都是吹牛角或者竹筒的声音,到处高喊捉特务,到处都群殴知青。
重庆知青曾先龙插队显周公社安乐1队,那里离马儿惨死的大云四队只有几里路。8月19日那天早上,曾先龙准备出门去赶场,一向很温厚的生产队长忽然很严肃地拦住曾先龙,就像黄天勇告诫王信年一样,叫他今天哪里也别去,就在家里呆着。曾先龙感到莫名其妙,坚持要去赶场。队长一反常态,不由分说把曾先龙推进生产队的保管室反锁起来。曾先龙被关在保管室里十分纳闷,正百思不得其解时,忽听见保管室后边的大路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伴着激昂的喧哗声,其中一个声音说:“这院子里有个知青叫曾先龙,我们先去打死他!”说着一大群人就涌进院子来。这时生产队长迎上前去说:“曾先龙没有在家,出去了。”那些人就拉着队伍很失望地离开了。曾先龙躲在保管室里吓出一身冷汗,事后他说:“要是没有队长保护,我那天说不定和马儿一样下场。”事实上,那伙人离开安乐大队后就杀到了大云4队。曾先龙后来任忠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成了知名文物考古专家,与我关系甚笃,为几十年间不可多得的朋友。这段经历是他亲口所述。
插队显周师联5队的知青刘作舟是重庆11中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酷爱物理,要是文革迟来几天他就上大学了。他在知青群体中算最“高龄”的,比起初中一年级的马儿,他高出五个年级,下乡时就已经21岁了,所以他绝不会像马儿那样不懂事。他从不惹是生非,一直在村里老老实实地劳动。8月19日,他到11中校友、插队师联4队的知青陈以其那里串门。那天天气炎热,他二人正在院子里光着膀子乘凉,忽然外面杀声震天,冲进一群手执器械怒气冲冲的农民,为首一个高举着亮闪闪明晃晃的“坡刀”。坡刀是用于铲草的,有些像古代的朴刀,四尺长的刀柄,一尺长四寸宽的刀锋,刀背略弯,使用时人站在田坎上居高临下往下砍,把田坎背上的杂草连着泥土像切豆腐似的削去,很是惬意,由于经常使用,刀锋都很锋利。
刘作舟戴着眼镜,看不大清楚,等到看清楚时农民们已经冲到眼前。为首那位高举起坡刀劈头砍下,刘作舟举起右手去挡,只听见扑哧一声,右手从虎口处砍下,大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裂为两块,半个手掌翻向一边软软地耷拉下去,还剩一点皮肉连着。
那个手执坡刀的人杀得兴起,转身又挥刀向陈以其砍去。陈以其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把长长的坡刀已经“嚓”的一声砍进他的右手臂,骨头马上就露出来了,手臂上厚厚的肉全部翻开。他倒到地上,坡刀又砍进他大腿,血直喷。这些都发生在一瞬间,等到院子里的社员们来劝解时,刘作舟陈以其已经满身鲜血淋漓。
刘作舟陈以其都是在农村表现很好的安分守己的知青,那些打手杀红了眼,根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知青就不放过。当天,刘作舟陈以其二人被抬往拔山医院,随后又火速转到重庆治疗。刘作舟经过抢救,右手留住了,但手指功能从此严重退化,握合能力很差,好在经过长期恢复训练后,右手能够勉强握住电烙铁。刘作舟视无线电为生命,天天都要使用电烙铁。他伸出并不灵活的伤痕赫然的右手说:“只要还能够拿住电烙铁我就不怕”。知青返城后,刘作舟是重庆广益中学的物理老师,2008年不幸死于癌症。
鸡公——万启福也于2008年死于癌症。
2005年7月30日,我在重庆杨家坪见到了年已54岁的陈以其,他撩起衣袖和裤腿,38年前的累累伤痕如同指头粗细,依然疙疙瘩瘩地凸起,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师联4队离马儿惨死的大云4队相距10馀里,可见当天的战线之长,战场之广,而这仅仅是当时的区区一角而已。在那个时段,全县都爆发了围攻知青的运动战。黄金公社、绍溪公社、黄钦公社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殴知青事件。我的朋友、落户绍溪太平大队的谢崇华与同大队的重庆知青谭思亮等八人被围在一个地坝里打得头破血流,谭思亮的脑袋被一根尖利的錾子刺穿。与马儿差不多同时惨死的还有黄钦公社知青陈斯伦。17岁的英俊少年陈斯伦被潮水般的农民围堵,不得已躲进公社诊所的楼上,疯狂的打手们爬上屋顶揭开屋瓦,把鸟枪伸进去朝着他开枪,他当即毙命。闻讯赶来的知青们抬着他的尸体来到县城游行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我正好从复兴公社赶回县城,目睹了这一感天动地的场面。知青们从全县各地乡下汇集到城里,大约有千人之众。陈斯伦的母亲和姐姐也从重庆赶来了。知青们从印刷厂找来白色的边角纸条,洒满了大街小巷,又在大礼堂楼下布置了灵堂。陈斯伦的遗体用冰砖冷冻着,供人们凭吊,他头上的枪伤明显,面部淤血青紫成斑惨不忍睹。傍晚时分,数百个女知青在广场上放声痛哭,泪流成河,哭声凄婉撕心裂肺,汇在一起如同浪涛汹涌,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面对此情此景,未有不动容者。在强大的压力下,县上同意在大礼堂召开了陈斯伦的追悼会,我作为知青的一员参加了追悼会。会上,陈斯伦年约40左右的母亲泣不成声,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同时也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要求广大知青“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
【8】这一切到底是谁之过?
显周乃至忠县广大农村所发生的痛打知青的运动,其实是县上有意部署的一场所谓“打击流氓阿飞”的运动,如果没有统一部署,很难想象如同散沙的农民们会在同一时间高度的组织起来开展大规模的行动。县上的初衷只是想“打击”一下,完全没想到会造成如此惊天血案。
马儿案发生时,我还在复兴公社插队,复兴公社也按照县上的指示部署了“打击流氓阿飞”的运动,并层层传达到了生产队。我所在的水坪6队是由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家住但家冲的刘宗信组织社员大会传达的,我清楚记得刘宗信在会上讲:“公社布置了,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好木棒,像这么长的木棒。见到流氓阿飞就打!”他在说这么长时还双手比划了一下。我们插队那一带知青惹是生非的不多,所以最终没有酿成大规模的痛打知青悲剧。
而在后乡就不同了,知青惹祸的事时有传闻。一些知青到处惹是生非偷鸡摸狗甚至无恶不作,激怒了广大农民群众,最后矛盾激化,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最著名的是发生在三汇公社的“六三事件”。1969年6月3日,一群知青在三汇场上撒野,出手打人行凶,扰乱市场。当时正值三汇赶场,赶场的农民人山人海,人们惊恐万状,相互践踏,鸡飞狗跳。这伙知青野性难驯,竟然冲进供销社打破大酒缸。三汇场如同经历匪患,凌乱不堪。知青们玩得兴起,又赶往20里外的金龙公社,抢走公社的火枪,一路胡作非为,农民望而掩门,避之唯恐不及。此事后来被严肃追究,为首者被判刑入狱。
那些知青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成了革命小将,他们共同的名字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简称红卫兵。他们如同天兵天将,以横扫一切的气势,把社会闹了个底朝天。那时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都可以任意地侮辱所有当权派以及所有的黑五类。正是由于他们过于疯狂燃烧的激情,才使毛泽东顺利地实现了打倒刘少奇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政治目的。那时的中学生成了政治舞台上冲锋陷阵的主要群体,其社会地位显赫不可动摇。谁知仅仅才红火了两年,所有中学生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抛弃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去接受那些他们从来看不起的农民的再教育。从相对条件优裕的城市一下到了荒凉贫穷的农村,从天兵天将一下变为农民,犹如突然从云峰上跌落下来,其心理落差岂可言喻。在此情况下,一些知青便自暴自弃,好逸恶劳,甚至为非作歹制造事端,而农民则是无辜的受害者。那时农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集体生产的粮食除了上缴国库外,自留部分根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对于那些只会分粮食却不会干农活的城市知青,农民当然心存不满,只是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接受而已,而怨恨之情早在心中扎下了根,一旦有机会就要宣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双方都充满了怨气,怨气越积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终于引爆。
马儿到显周时,并没有因为环境和身份的改变而完成角色转换,思想还停留在文革的打砸抢氛围中,身上还保留着无法无天的红卫兵习气,说穿了就是痞子气,因为红卫兵运动的实质就是痞子运动。显周不少老乡向我讲了一大堆马儿的劣迹。
有一件流传很广的事是,一天晚上,月明星稀,马儿和几个知青在大云水库边乘凉,大云水库位于大云5队,就在大云包的山下。这时有十来个新立公社双福大队的农民扛着从几十里外的精华山上砍回的树子经过水库,马儿大喝一声拦住他们,知青们一拥而上把树子全抢了。夜色中农民们不知道四周有多少知青,吓得魂飞魄散四处逃命。双福7队的农民肖本全慌不择路,跑到大云包上,钻进黄天雪老师家的猪圈里躲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黄心云看见他时,他还发抖。
农民手中的树子是来之不易的。大炼钢铁运动已经将树木砍伐殆尽,农民用材非常困难。离显周数十里的精华山上还保留着部分森林,但已经封山育林,由林场管理着不能砍伐,违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逼着迫切需要木材的农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护林员进山盗伐。这是一件非常艰难风险极大的事。进山盗伐的农民必须在天亮前出门,翻山越岭几十里,进入密林里藏起来,等到安全的时候才动手砍伐,然后在林子里等到傍晚时才悄悄下山。一根树子少说有百多斤,扛着树子穿越深山密林走过悬崖峭壁,是多么艰辛。经过一天担惊受怕挨冻受饿劳累已极,在就要回到家门口时,树子却被抢走,其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由于自己知道盗伐是非法行为,所以当马儿拦路抢夺时也不敢据理力争,只有自认晦气。
马儿的本意其实也不一定就是抢夺,充其量就是恶作剧,闹着好玩。他还有一个威胁人的理由,就是不准盗伐国家林木。他年幼无知瞧不起农民,没有把农民放在眼里,更不知道这样会使人家受到伤害。人家辛辛苦苦扛回的树子,马儿像开玩笑一样,转手用一两元钱的低价就出卖了,可见他真是闹着玩,并不是以占有财富为目的。
马儿一伙在大云5队曾经百般戏弄黄天勇,据说他们硬要黄天勇陪着去大云水库游泳,按着黄天勇的头呛水,还把黄天勇四肢提起晃荡。这是黄天勇带头残害马儿的主要原因。
那时知青生活艰苦,营养极差,到处都有偷鸡的事情发生。忠县农村千百年来的养鸡方式都是把鸡圈修在室外,由于知青偷鸡成风,农民们被逼着把鸡圈搬进了室内,从此流传千百年的养鸡方式彻底消失。马儿毫不例外,一定也有过多次偷鸡的记录,或者即使不是他,后来也算到了他头上。
马儿和鸡公更多的是欺负地主富农这些政治贱民,地主富农家的南瓜茄子还没有长大,他们就摘来扔了。甚至有很不靠谱的传闻说,他们在大云5队硬要国民党保长黄正栋的闺女给他们洗澡。
越来越多的真真假假骇人听闻的传闻将马儿之类的知青完全妖魔化,没有谁会去追问传闻的真实性,但是农民仇恨的火焰却因此被点燃了。当忍无可忍的农民组织起来后,真的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吞噬一个马儿只是小菜一碟。
但是如果深究原因,就应该归咎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红卫兵运动,马儿就不会染上一身痞气;如果没有知青下乡运动,马儿就不会伤害农民的感情。反过来说,朴实本分的农民们如果不是感情被深深的伤害,也不会变得那样暴虐凶残。
县上后来处理了打死马儿案,将5队队长黄天勇作为主要责任人绳之以法,判处五年徒刑。黄天勇刑满后回家成亲,生了两个儿子,不幸老婆身患癌症,因家庭贫困债台高筑,两个儿子无法找对象,老婆在贫病中死去,黄天勇忧愤成疾,患精神病多年,今已70多岁,到我写作此文时依然晚景凄凉。
第七章 “三分之一”
【1】 认识沈昌荣
中国的政治术语极为丰富,足以编写一部《政治术语大辞典》,否则过不了多久就完全无法解读,比如“三分之一”,现在谁还知道?很有趣的是,我就曾经参加过“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名称,和其它所有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也是毛泽东的创举。这位被吹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的人在无数次地把贫下中农尊为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后,又忽然发现这些主力军其实是自私落后的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要不断地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73年,毛泽东发出了“面上的工作要先抓三分之一”的最新最高指示,具体讲就是,把所有地区划为三等分,每次在三分之一地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三次搞完,这就叫“三分之一”。
忠县县委在1973年秋末开始了“三分之一”运动,显周公社名列其中。全县从县区社三级机关抽调人员组成庞大的工作团,分派到公社叫工作队,深入到大队叫工作组。这种气势宏大的运动团队我读小学时就听父母说过,想不到的是,直到我成年后,这种制度还在继续,而且我是其中一员。
我被公社抽调参加了显周公社三分之一工作队,和来自拔山区市管会(后来叫工商所)的沈昌荣搭档,一起进驻沥石大队,沈昌荣任工作组长。
沈昌荣个子高大,满脸络腮胡,大眼睛常常瞪着,嘴唇上翻,戴着一顶黑色呢子帽,披着一件长长的黑色棉大衣,模样威严,嗓门粗大。据知,他是近邻花桥公社石堰大队人,早年曾参加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后来任过拔山区供销社书记,是钱金益的前任。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沈昌荣居然不叫我老陈而叫小陈,他是惟一叫我小陈的人,在听惯了老陈后,觉得很新鲜。他看上去很威严,接触后才知道,他其实非常随和,善解人意。在我眼中,他的农村工作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走到哪里遇到任何问题他都能驾轻就熟从容应对,而且能迅速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讲政策,谈生产,话家常,批林批孔,样样都行。我想,要是我有他那么丰富的经验就好了。我特别佩服的是,他讲话从来不要稿子,一口气讲一两个小时,说得头头是道,唯有一点我很不习惯,每次在沥石大队开会开到深夜时,人们都盼望早点散会了,他却说,我还讲“最后五分钟”,这最后五分钟一般都将近一个小时。
我和沈昌荣主要住在沥石八队潘全槐家。潘全槐是大队副书记兼副业大队长,已经70多岁了,满脸沧桑,头上永远包着帕子,随时露出苍老的笑容。此前,因为他是副业大队长,我已经很熟悉。潘全槐老人的儿女都已经成家,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在家中。平时家里就他和老伴女儿。我们按照规矩,在墙头贴出一张《吃饭登记表》,每吃一顿饭,就在表上画个圈,月底有多少圈,就按照每顿饭0.11元加三两粮票付账。虽然潘全槐老人一再谢绝,但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给他。在粮食紧张的年代,谁承担得起两个客人长住在家里?
我和沈昌荣每天晚上抵足而眠,他会给我讲一些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他说他曾经冒着炮火攻入平壤,“平壤好一点的街道也就只有那么两条”……他说“四清运动”时他也是工作组成员,那时万县地区工作总团的团长是地委书记王仲英,王仲英对人粗暴,喜欢拍桌子训人,“我也当着王仲英拍过桌子”……他说,不论兄弟感情多好,只要结婚后老婆告了枕头状,就会伤害兄弟感情,“我们兄弟感情是最好的,哪个有我们好?可是后来也……”有一次他很神秘地轻轻告诉我说,供销社的工作,只要是过尺过秤的,没有一个不贪污,除非笨得啃猪圈板,“小陈,你最好想办法离开供销社,免得以后搞运动走不脱。”他这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是拔山供销社的老领导,所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我当时就把我认识的供销社同事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难道他们都在贪污?
【2】美丽的萧家湾
沥石大队的大队部设在3队萧家湾,萧家湾是大队的政治中心,我们的许多活动都在那里进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萧家湾在1949年以前是地主萧玉涵的私宅大院,周围冈峦起伏竹树葱茏,大院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玉带般的小河,河里水草摇曳,鱼虾成群。主人别具匠心地将小河开了一个口子,将清清的河水引到大院前面像护城河似的筑了一个硕大的鱼池,池中种着荷花,池上是一座古朴的石平桥通向大院的大门。大院终年掩映在水光山色之中,气象氤氲,风韵典雅。依山就势筑成的大院呈不规则形,周围是曲折有致的青砖封火墙,院内又分为两个小院,房屋为木结构青瓦房,石坝台阶别有天地。最美丽的是大院门口高高耸立的一座五层高的碉楼,碉楼全用青石砌成,巍峨挺拔,每层楼都凿有圆圆的枪眼,在第五层的一角用石条横伸出来建了一座小小的望楼,恰象在肩头直举起一支手臂,造型奇特峭拔,引人注目。碉楼顶四角飞檐高挑,势欲凌风而去。
1949年后,萧玉涵被整得家破人亡,院子全部作为“胜利果实”分给了贫下中农,从此大院被日益蚕食趋于荒废,鱼池改成水田,碉楼改为代销店,整个大院凌乱不堪。但是,毕竟大院的整个形胜尚在,风韵犹存,所以在方圆几十里内依然是最美丽的风光。
住在萧家湾的人依然以萧姓为主,三队队长萧应选就住在这里,他已经70开外了,是全公社最年长的生产队长。他好像没有儿子,招了一个姓冉的转业军人做上门女婿,添了一个外孙女,叫小红,那时只有几岁。
住在碉楼里经营代销店的人叫萧显发,老婆姓董(好像叫董德民),这两口子一直想生个女儿,结果一连生了七个,全是儿子,七个儿子每天张着嘴巴要吃饭,把两口子累坏了。萧显发的代销店属供销社管,故与我也很熟悉。
住在萧家湾堂屋左边的是一位重庆女知青,叫汤玉辉,她是重庆39中的初中三年级学生,从1969年初来到这里,已经四年多了,年已23岁,因为出身问题,一直陷在这里。汤玉辉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面容清秀,梳着两条长辫,然而明澈的眼眸里却时时流露出深深的忧郁。
30多年后的一天,我在重庆和杨秀维曾先龙等几个老知青朋友重逢,醉得飘飘欲仙,忽然有人说:“走华子家去”,于是一行人踉踉跄跄地到了华子家,华子也是老知青。华子见到来了这么多朋友,马上打电话叫老婆回来备办晚上的饭菜。一会儿就有一个50多岁的头发花白的女人赶回家来了。我觉得那女人有些面熟,定睛看去,依稀仿佛当年萧家湾的女知青汤玉辉。
我便试着问:“你以前当过知青?”
她说:“是啊。”
我又问:“你是在忠县插队吧?”
她有点惊讶地望着我说:“是啊。”
我接着说:“你是在显周公社吧?”
这下她更惊讶了,她没有再回答,而是用非常疑惑的目光迅速地扫视着我。
我此时相信她就是汤玉辉无疑了,就说:“当年是不是有一个工作组在你们沥石大队,工作组里有一个年轻人叫陈仁德……”
我说到这里,她已经恍然大悟,连声说:“哦……哦……”
人生就有这么奇特的巧遇!
我和汤玉辉说起萧家湾,她比我印象更深,立即就说起那座美丽的碉楼,她在那里六七年啊。这时我告诉她,萧家湾的碉楼早就没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显周公社修建办公楼,因为缺乏木料,把碉楼全拆掉获得了一些废旧木料,美丽的碉楼就永远消失了。其实那点废旧木料能值多少钱啊,公社获得的残值,远远不及他们毁掉的价值。
这几十年里,不知道多少美丽绝伦的东西被那些所谓的革命者们毫不心疼也毫不手软地毁掉了呀!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