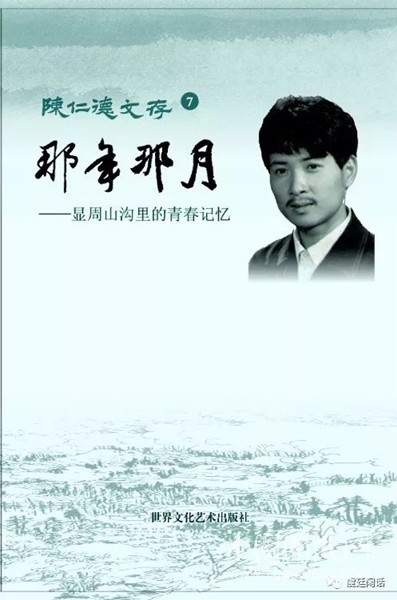
【5】与张亮的奇特邂逅
10月里的秋旱仍未解除,人人都渴望着老天下雨。这一天,天气沉闷难当,天空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往下压,让人周身不自在。根据经验,这正是天公在酝酿着一场大雨。大雨到来前往往是沉闷不堪的,整个天空充满悬念,不知到底什么时候雨才能落下来。有时酝酿了很久,忽然一阵风把天上的积云吹走,天空又重新晴朗起来,让人空等一场。一旦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那就是痛快淋漓,人人称快。
由于这天不逢场,场上行人寥寥无几,很是萧条。下午5点多,我拿着饭碗去公社食堂吃饭。当我经过诊所时,看见一个病人坐在诊所门前满是尘土的街沿上,头上缠着一条灰白的帕子,衣衫不整,身子有气无力地靠着墙壁。那是一面土墙,墙上粉刷的石灰已经大块大块剥落,露出粗砺的夯土,那个人的后脑勺就仰着靠在夯土上。
这是诊所门前惯见不鲜的情形,来就诊的农民们经常坐在那里,像难民一样。
我从那里走过时,恍惚听到有人叫“陈七”。陈七就是我,我在家里排行第七。我疑心是幻听,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叫陈七。于是我快步走过。
“陈……七……”声音再次传来。这次我听得真切。
我回头看去,那坐在地下尘土中的人向我轻轻地扬了扬头,又叫了一声“陈七”。
我定睛看去,不禁大吃一惊。那人竟是忠县城关民中初67级同学张亮。只见他脸色蜡黄,双目黯淡,额头上印着一个紫黑色的火罐印,一副标准的农村病人模样。
我上前把张亮拉起来,感觉他的手有些发烫。
“我病了,发高烧,实在受不了才到显周来看病的。没想到意外见到你了。”张亮说。
我把张亮迎进我的小土屋。
张亮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父亲张执丹先生曾任忠县云根小学校长,1949年后父母都是忠县师范学校教师,由于是所谓“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兼以他们不幸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之类的组织,使得他们成为政治贱民,直接祸及子女。张亮在学校时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比我高一个年级,那时我14岁他15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他一家兄妹五个全部都“光荣”地下乡插队当了农民。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都长期受到歧视无法返城。他插队的地方是精华公社贯子大队,离显周约有15里山路。站在我屋后的断崖边,可以远远地看见他所在的村落,在一片山岭之巅,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白色碉楼,他就住在碉楼上。
用狼狈不堪来形容此时的张亮一点不过分,他的装束神态和流浪汉差不多。细听他讲来,却原来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大挫折。
一向热爱学习成绩优异的张亮,听说今年国家要招收大学生,就兴致勃勃报名参加,由于他在农村劳动表现非常突出,学业也好,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赢得上下一致赞誉,公社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在向新立区推荐时,把其他知青都砍掉了,只推荐了他一个人。在当时这是极不容易的,张亮为此很高兴了一阵子。他在劳动之余挑灯夜战复习功课,最后在全县大考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正当他以为这次可以实现理想时,万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辽宁省某个考场和他同时参加考试的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闹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事来。
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6月30日的理化考试中,张铁生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对自己的低劣成绩进行辩解,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他这封信于8月10日被《人民日报》发表,后又被《红旗》杂志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为此均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这一来,当年的文化考试全部被否定,张亮没有高兴几天就掉入冰窟,陷入绝望。
我插队在复兴公社的姐姐陈琳和张亮也是同样的遭遇。姐姐参加文化考试,名列公社第一,正当全家为之庆幸时,理想却被无情地击碎。姐姐这一年25岁,是高考的最后年限,此后就终生没有机会了,姐姐伤心欲绝,独自痛哭到天亮。直到老年,姐姐仍然对这一段往事无法释怀。
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被摧残的青年人杰何止千千万万。
【6】风雨之夜潘经理逐客
遭受沉重打击的张亮此前刚经历了一场痛彻肝肺的失恋,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一个美丽少女离他而去,双重打击之下他彻底崩溃,看不到希望了,这时疾病也向他袭来,他一下倒床不起。农村没有医药,头痛极了,他就像农民一样用帕子把头包起来;发高烧,就请农民在额头上打一个火罐。硬挺过了两天,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这才不得不请一个农民搀扶着走过15里山路来到显周卫生所。张亮说,到显周来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听说显周公社来了一个民中同学,不知道究竟是谁,希望能顺便打听打听,当街头偶然看见我路过时,才知道这个同学就是我。
想不到我们是如此重逢的。
经过打针服药,下午,高烧退去了,张亮的精神有所好转,我挽留他住一天再养一下,不要急着回去。他也很乐意向我倾谈他的故事,就留下来和我共榻。
晚上我们在灯下继续聊天,回忆中学时代,讲述知青经历,话匣子打开就没完没了。到了10点后,有人敲门,随即传来潘经理的声音。我打开门,潘经理就干咳着走了进来,他的脸色凝重而严肃。
“这位是知青吗?”他问。
“是的,他是精华公社贯子大队的知青。”我赶紧回答。
“我们这里是经济部门,不能留客住宿!”他把脸转向张亮,声音很低但是口气很重地说。
潘经理要赶张亮走!
我马上解释:“张亮和别的知青不一样,他劳动积极,表现很好。”
“老陈你不要说,经济部门不能留客住宿,这是规定,出了问题哪个负得起责任!”潘经理向我摆摆手,“现在的社会复杂得很,哪个认得到他?哪个来证明他的身份?”
“诊所丁医生认识我,我们在拔山区医院见过。我叔叔张笃清是拔山医院的书记。”张亮接过话说。
“那你去喊丁医生来证明。”
丁医生叫丁明文,是显周诊所所长。我和张亮马上跑到只隔十多米远的诊所叫丁医生。丁医生住在楼上,此时已经睡了,闻声走下楼来,揉了揉眼睛说:“是的,是的,是张笃清的侄子。我见过几次。他发高烧,今天来看病的。”
这下张亮的身份明确了,该没有问题了吧?
“不行!经济部门不能留客!”潘经理依然坚持着,让我大吃一惊。显然他没有想到丁医生真的认识张亮。“你们去公社说清楚。看公社怎么说。”
我不得已又带着张亮到公社去找公安员黄承华。
谁知黄承华冷冷地说:“经济部门有规定,不能留客。你叫他走就是。出了问题不得了,这是原则问题。”
原来潘经理先就给黄承华说过了。
张亮看见形势很严峻,很平静地说:“陈七,不要说了。我走就是!”
这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也没有办法了。只有把张亮“礼送出境”。
那晚没有月亮,天地间漆黑一片,张亮连电筒也没有一个,就在黑暗中从容地离去了。在显周场口,我看见张亮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只在几步外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回到我的小土屋,我把潘经理黄承华恨得要死,一个比芝麻还小得多的官,居然可以如此的无礼。我深感对不起张亮,惭愧不已。这时忽然一声闷雷,紧接着开始下雨,那场酝酿了很久的大雨终于倾盆而下了。我猛然想起正在崎岖山道上摸索的张亮。那是一条艰难的山路,悬崖陡坎深涧急流,他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病情稍有好转,此时他该如何是好?
张亮以惊人的毅力在风雨中、黑暗中走过了15里崎岖山路,满身泥水回到了贯子大队,真是奇迹。
恢复高考后,在农村已经度过了十载寒暑的张亮,以优异成绩考入重庆大学,他的命运彻底改变。后来他是四川外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系总支书记,是我不可多得的挚友。他的女儿留学欧洲获博士学位,已经在海外安家。我中年后在重庆定居,经常和张亮聚会,每当谈到那段往事时他依然念念不忘,说当时主要是不想让我为难,否则他不会冒着风雨在黑暗中离去。而我,心中总是充满内疚。
第三章 极度匮乏
【1】小学生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
物资的匮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作为物资供应部门的供销社,经常为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要求而备受群众责难。
糖,成了比稀有金属还珍贵的物品,供销社的货柜里难得一见糖的影子。农民们别说吃糖,就是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在林林总总的票证中,有一种是糖票,是供销社自己油印制作的火柴盒大小的一张小票。凡是生了小孩,就可以领取一张“婴儿糖”票,凭票可以在供销社购买一斤白糖,这是给产妇的惟一优待。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优待,在实际执行中却是另外一回事。产妇手里拿着“婴儿糖”票,一次次地到供销社副食品门市来买糖,结果都是缺货,无法供应。那张薄薄的火柴盒大小的“婴儿糖”票极为宝贵,家庭主妇们会精心地保存着,生怕揉坏了,可是,在一次次奔走供销社之后,小票终于残缺不堪,但是,即使如此也还要保管着,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买到白糖。
有一次,潘经理指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对我说:“这个小孩子直到现在还没有买到‘婴儿糖’,她妈妈最近还拿着糖票来问过我,我叫她把糖票继续保存好,今后要兑现”。我极度震惊。一个人从出生到上小学,竟然还没有买到那一斤可怜的“婴儿糖”,也就是说,这个小学生至今还不知道糖是什么滋味!
天啦!
潘经理却很平静,说:“这种情况多的是,一点不稀奇。社员们也有办法,种甘蔗嘛。坐月子的时候把甘蔗砍下来削去皮,切成小颗粒放到沙钵里冲,冲出来的甘蔗汁就拿来喂娃儿,等于就是糖了。”潘经理说。
农村女人之命苦,可以想见。
有一次潘经理从拔山回来,传达区供销社会议精神,说:“现在农民买不到饭碗,怎么办?有办法!区里会上讲了,可以用水瓢当饭碗。”他的话音刚才落地,坐在旁边的收购门市部营业员、老志愿军战士伯有训就冷冷地说:“还有办法,用石头打噻。”大家一起哄堂大笑。石头打的是猪槽,喂猪用的,乡下互相调侃嬉骂的话就是说人家的碗是石头的,意思是说人家是猪。与石碗同音的“十碗”都成了忌讳。待客时上菜必须避开十碗这个敏感词,可以是九碗,也可以是十一碗,绝不可以用十碗菜待客,那等于侮辱客人是猪。据说还有的地方,因为主人疏忽,不小心上了十碗菜,客人当场把桌子掀翻了拂袖大骂而去。
供销社偶尔购进一批草纸都要开后门悄悄卖。那是什么草纸?粗糙得像树皮,厚厚的,提起一抖就灰尘飞扬,造纸的原料是稻草,从纸上随时可以把没有化尽的稻草疙瘩扯出来。这种草纸现在早该进博物馆了,可是那时却很稀有。不过,话说回来,用得起草纸的都是公社干部之类的人,用来做手纸或者做女人的卫生纸,而农民对草纸基本没有需求。农民家庭几乎百分之百从来不使用手纸,他们代代相传的都是使用竹片。你到任何一个农民家里去,都会在猪圈旁看到一束靠在墙头的做手纸用的竹片,农民们大便后就顺手在墙头折下一节竹片来刮一下屁股。农村中的妇女更恼火,根本谈不上任何卫生用品,她们发明了一种很无奈的做法,把烧过的细细的草木灰灌进一条长长的小布口袋,用来对付每月一次的烦恼。
供销社的职工是很受人羡慕的,因为他们相对说来比一般人掌握物资的机会要多,拥有某种可怜的特权。
那时已经开始引进日本尿素(化肥),人们惊奇地发现,日本尿素的包装袋是一种尼龙材料,可以用来做衣裤。长期的布票政策,已经使人们对布匹产生了一种崇拜。我的一个文友曾经讲过他自己的一段经历,当年别人给他介绍一个女友,他兴致勃勃去相亲,见面后双方都满意,但是后来却告吹了。媒人告诉他,对方什么都满意,就是不满意他一米八的身高,害怕今后布票不够用。这种幽默现在听起来很开心,那时却伤心。日本尿素包装袋的出现,使供销社的职工趋之若鹜,纷纷争购来做衣裤。这就使街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由于日本尿素包装袋上印着“日本某某株式会社尿素”字样,做出的衣裤上都保留着这些清晰的字样,走在大街上,路人一看就知道是供销社的人来了。一首民谣便流传开来:
供销社的干部一大路,
穿的抖抖裤。
绸不像绸,
布不像布。
前面是日本,
后面是尿素。
【2】 吃肉何其难
肉食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国家工作人员每月可以凭票购买一斤带骨的猪肉。在漫长的30天中,就眼巴巴地指望着那可怜的一斤肉“打牙祭”。而广大农民则无缘享受这一斤宝贵之极的猪肉,农民们辛劳终年,只有三次享受猪肉供应,一次是端午节,一次是中秋节,一次是春节,每人每次半斤。365天里只有1斤半肉(市斤)。
农民吃肉只能靠养猪解决,可是,在那个贫困之极的时代,人的肚子都填不饱,以前猪吃的东西比如米糠等,都被人吃了,拿什么喂猪呢?凑凑合合地把猪喂大养肥,都没长多少肉。国家的政策是“卖一留一”,就是说,农民要喂两头猪,先将其中一头卖给国家,由食品部门发给“留猪证”,另外一头才可以留给自己宰杀。杀猪匠到农民家杀猪要先查验“留猪证”才可以奏刀。事实上走遍广大农村,都难得找到一家农民能够养两头猪,养一头猪都很难。只养一头猪怎么办?国家的办法又来了,只养一头猪就要卖“边口肉”,把一头猪从中间解剖,一边交给国家,另外一边自食。国家还规定,“硬边”上交,“软边”自食。什么叫硬边软边?杀猪后顺脊椎分解,骨头稍多的一边为硬边,另一边为软边。硬边的重量大于软边,养猪的农民只能吃软边。
每年冬至后,农民开始杀猪,这是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辛辛苦苦一年,终于可以杀猪过年了,闻讯赶来吃“刨汤肉”(杀猪宴)的亲友们像过节一样穿得比平常略为干净一些,坐在地坝里的板凳上。主人把杀猪匠请进屋,在院坝外挖一个大坑架上大锅,把水烧得滚烫,氤氲的热气随着寒冬的霜风四处蔓延,充溢着朴素的喜气。院子里的小孩子们一个个脸冻得红红的,手缩进破烂的袖口里,流着鼻涕围在一旁,眼睛直直地盯着大锅。主人把肥猪从圈里拖出来,肥猪知道末日来临了,死活都不肯就范,拼命地挣扎着,发出声声哀嚎。主人迫不及待地揪住硕大的猪耳朵使劲往外拖,杀猪匠也上前揪住另一只耳朵一起发力。肥猪蹬住四蹄,尾巴夹到屁股里,被拖过的地方划过深深的蹄印。终于,杀猪匠把肥猪按倒在地坝边先准备好的一块大石板上,肥猪侧身露出臃肿的颈项来。杀猪匠看准时机把亮闪闪的一尺多长的尖刀一下从颈项刺进去,直抵心脏。猪血霎时喷涌而出,流进石板下的木盆里。肥猪发出最后的惨叫,四蹄抽搐着咽气了。
杀猪匠把刚刚咽气的肥猪的后蹄切开一个小口子,把一根拇指粗细的四尺长的铁杖——当地叫“挺杖”,插进小口子,一寸寸地往里捅,一直捅到猪耳朵部位,再把“挺杖”退出来,这样肥猪全身就贯通了。这时杀猪匠俯下身去用嘴巴对着猪后蹄那个小口子往里吹气,一股股的气就从刚才打通的通道进入肥猪的身体。杀猪匠憋足了气,额头的青筋暴起像弯曲的蚯蚓,脸涨得通红,吹一阵,换一口气再吹,竟然把一头肥猪吹得像气球似的鼓起来,四只猪蹄都直直地伸着。这时便把口子用绳子系紧,把圆滚滚的肥猪放进大锅里翻来覆去烫,一边烫,一边就飞快地用一个铁刨子褪毛,看着看着,满身是毛的肥猪就变得光生生的了。
接下来把肥猪倒挂在一棵树上,杀猪匠熟练地举起刀从尾部一分为二,然后像庖丁解牛那样,把肥猪划成一块块的,当然,要先把硬边留给国家。
杀猪匠分解肉块需要很好的手艺,主人要先把坐礅(屁股)肉划成若干“礼信”,即送给亲戚的礼品。每个“礼信”薄得只有两指,但从侧面看却很宽,有五指多。一头并不大的猪宰杀后除去内脏和杂物,总共可能有七八十斤肉,把硬边留给国家,就只剩下三四十斤,去掉“礼信”十来斤,可能还有二十多斤,这时杀猪匠把刀一挥,切下好几斤一大块,交给主人拿去做“刨汤肉”,这样,一头猪就剩不了多少了。
但凡在杀猪的那段时间,大队书记每天都要“深入”到院坝,等到“刨汤肉”香气四溢地端上桌时,书记便在上座上吃得满嘴流油。
养猪最辛苦的是家庭主妇,可是吃肉时家庭主妇按照风俗却不能上桌,她一直在灶屋里忙碌着,等到一家之主的丈夫在桌上陪客人吃完后,主妇只能喝一点残汤。我毫不怀疑,那时大量的农村家庭主妇一年到头根本没有吃过一次肉。
【3】 阎玉成怕把三两米搞脱了
掌管肉食的食品门市经管人成了万众翘首的人物,无人不想巴结,从而偶尔买到一点点肉食。但是,内部对此有非常严格的制度,经管人一般不敢随便卖人情,而且的确也没有多少肉可在计划之外出卖。这时又有一个空间出现了,严格凭票供应的是猪肉,猪的内脏,我们那里俗称猪杂,却不在计划之列。于是猪杂就成了非常诱人的宝贝,人们千方百计都想买一点猪杂,哪怕是一叶肝,或者一条舌。
像显周这样的小乡场,每次赶场只宰杀一头猪,又能有多少猪杂呢?
公社食堂每月吃两次肉,每次半斤,一律做成粉蒸肉,每人一碗。炊事员何良木事先要算好人数,哪些人吃了,哪些人外出未归没有吃,都要记上,这是不能够轻易被剥夺的权利。吃肉时差不多职工们都到齐了,食堂里显得有些拥挤。何良木很神圣地把叠成几层的大蒸笼揭开,一时热气腾腾,肉香扑鼻。何良木的烹饪手艺不算好,但是,他做的粉蒸肉却是一流的好,吃进嘴里香透了,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心想慢慢受用,却不小心早就滑下肚子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走遍天涯海角,似乎只有显周那个山沟里的炊事员何良木做的粉蒸肉最好吃。
由于肉食的极度匮乏,使得许多人为此而失去尊严,失去贞操,甚至伤风败俗。这是个人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与显周相邻的花桥公社,一个年轻女子想尽办法都买不到肉,万不得已只好跑到食品组经管人阎玉成的床上去躺着,自愿交欢。阎玉成是个北方来的老干部,年轻时不慎被炸去了右手掌,只剩下左手,人称“一把手”。他曾经是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在反右运动中被无端革职为民下放到花桥,老婆也和他离婚了。他虽然渴望女性,但他深知政治运动的残忍,而男女问题那时都是要上升到政治问题上来说的。当他面对那个躺在床上的年轻女人时,一点不敢轻举妄动,用浓浓的北方腔对那个女人说:“要割2斤肉可以。我不搞你那个灯,我怕把三两米搞脱了。”三两米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称,三两米搞脱,就是因此被开除公职没有了饭碗。
我认识阎玉成,他和我同属拔山区供销社。若干年后,他的女儿阎兴惠嫁给了我的朋友向兴忠。他怕把三两米搞脱而拒绝女色诱惑的事情成为经典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人谈起,我也曾向向兴忠证实过确有其事。而故事的背后却发人深省,为了买一点肉,良家女子都愿意自荐枕席,何等酸辛。
【4】 米糠的致命诱惑
另外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则更让人感到沉痛。
显周公社前进大队(现在叫双塘村)有一对新婚夫妇,小伙子叫晏广(据说此人尚在,因涉及伤痛隐私,故此处用化名,读者谅之。)妻子名字不详,夫妇俩都喜欢唱歌跳舞,在大队算最优秀的。夫妇俩的拿手好戏是“打连箫”(也叫“打道钱”),各人手执一枝三四尺长的竹管,两端凿孔穿进铜钱若干,通体缠以彩条,挥动竹管并做出上下左右前后进退各种舞姿,让竹管依次碰撞在身体各个部位,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铜钱声。那时每个大队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表演一些简单的文艺节目。晏广夫妇都是宣传队的主力演员。由于他们比较活跃,加上前进大队就在显周场边,处于中心地带,所以和场上一些单位的人员比较熟识。那时显周粮点(区叫粮站,公社叫粮点)会计叫张蜀俊,和晏广也熟识。
农村人民公社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粮食紧缺。公社的体制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粮食产量很低(报纸上当然照例年年都是大丰收),每年生产的粮食除去上交“公字粮”“忠字粮”“爱国粮”,除去“储备粮”“种子粮”等等,留给社员分配的不多,每年总会有荒月。一年到头,很难吃一顿白米饭,都是瓜菜充饥。不要说粮食,就是糠也成了奢侈品。古往今来,谁都知道糠是喂猪的,没有人愿意吃糠。但是,时代不同了,在饥饿面前,糠也要吃。
公社的粮点掌管着糠的经营权,每当粮点加工一批大米后,便会有一批糠。这种糠磨得很细,比一般粗糠质量好,于是便成了粮点囤积居奇的宝贝,不是关系非常好的人,莫想尝到一点糠的味道。张蜀俊会计自然就成了实权人物,要想买糠,必须先打通他这一关。
晏广和张会计混熟了,就大着胆子开口买糠了。张会计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含含糊糊地支吾一阵。连着几次,晏广硬着头皮开口,结果都是一样,这让他颇有些困惑。
晏广不知道,当他在打主意买糠时,张会计却在打着他妻子的主意。他妻子新婚燕尔,青春靓丽,能歌善舞,在显周是数得出来的俏丽女人。这次,当晏广再次恳求买糠时,张会计先支吾了一阵,后来竟吞吞吐吐地把话说穿了,希望和其妻交欢。晏广当时大吃一惊,脸红到脖子上,半晌说不出话。
回到家里,晏广辗转反侧,一连几天彻夜难眠。一边是娇小的妻子,一边是诱人的细糠,他不知如何是好。在犹豫不决时,他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一下提醒了他,饿肚子最可怕,其馀都在其次。经过痛苦挣扎,他决定答应张会计的要求。
晏广鼓足了勇气,试探着对妻子说明情况,希望妻子能够配合,哪知话一出口,妻子就痛哭流涕,大骂他不是人。他也羞得满面流汗,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但是细糠毕竟对他有致命诱惑,他仍然打定主意要继续劝说妻子。
经过晏广厚颜无耻再三劝说,妻子不再争吵,只是默默地伤心流泪。晏广最后铁着心说:“你就当和我睡了一样,反正不会有人知道的。”妻子于是不再说话了。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