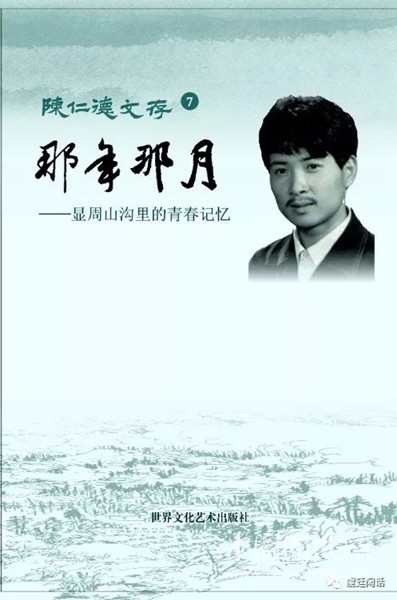
【8】走进显周“文化中心”
显周场的文化中心应该是显周小学了,这是一所完全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加上附设初中班,大概一共有十多个班几百学生。显周小学在显周场的入口一侧,校园顺着那条小溪修建,与显周场相对独立。没多久我就认识了小学的很多老师,经常和他们交谈,颇为投缘。
小学的校长叫王之碧,三十多岁,花桥公社宝胜大队人。其人嗓音洪亮,目光炯炯,干练精明,谈吐颇佳。我们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畅谈。有一天晚上,我们忽然有了酒意,可惜没有佐酒之物。王之碧校长笑着说:“有下酒菜呀。”他指了指屋角里堆着的一堆东西,原来是一堆红苕。“这个下酒好得很”,他俯身拿起一个沾满泥土的红苕,用指甲一片一片地剥去红苕皮,就像剥鱼鳞似的,等到剥出一小截时,就嘎嘣一声咬到嘴里脆生生地嚼起来。我也学他的样子拿起红苕剥皮生吃。就这样,我们咬一口红苕喝一口白酒,还真的是津津有味乐在其中。现在回忆起,好像鸡鸭鱼肉也不能与之媲美。
王之碧校长1975年提拔到拔山区做了文教助理,再后来又到县教育局任勤工俭学股长,现已退休多年。2011年春天,我乘车经过重庆龙湖西苑,在一个红灯路口停车时,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横道线上走过,我从侧面就认出他是王之碧校长。我大叫“王之碧”,他惊讶地回过头来。我把头伸出窗外连续大叫“王之碧”,他终于认出了我。就在这时,绿灯亮了,汽车启动了,我向他不停地挥手,直到汽车汇入拥挤的车流中。这时我又想起了将近40年前我们像剥鱼鳞似地剥开生红苕下酒的情景。
小学里最知名的语文老师叫刘尔彬,拔山公社双龙大队人,40左右,高高的个子,饱满的前额,风度儒雅,谈吐不凡。那时刘老师的两个儿子都还小,也在学校里读书,一个叫刘敏,一个叫刘波,都很聪明可爱。显周的乡村公路修通后,山民们第一次看到了手扶拖拉机,欣喜异常。刘老师为此创作了一首四川民歌风味的歌曲《卷洞来了拖拉机》,由他儿子刘波登台演唱:“……卷洞来了拖拉机,好不安逗逸。”刘敏和刘波在恢复高考后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很成才。
小学的美术老师叫黄天雪,显周大云大队4队人,头发略卷曲,面容瘦削,对人彬彬有礼。看他的面容,我以为他已经有30多岁。一次交谈时,他说:“我从20岁开始当民办老师,已经奉献了八年青春”,说这话时他伸手比了一个“八”字。这时我才知道他只有28岁。在偏僻的山乡里,黄天雪老师算得上是很有才气的,他通过自学,写得一手好字,也有较好的美术才能。我想,他如果生在另外的环境,比如生在大城市,很有可能要成为优秀的美术家。
黄天雪老师的妻子叫秦大惠,在家里务农,是个勤劳善良的女性。黄天雪老师带我们去他家做客,秦大惠总是非常热情。那时已经开始提倡计划生育,黄天雪老师属于计划之列,他考虑到健康原因,拒绝做绝育手术。他认为不必绝育,只要靠意志就可以避孕,这一说辞被王之碧调侃为“意志避孕法”。没有多久,秦大惠又身怀六甲,大喇叭里高喊着秦大惠的名字,通知她去引产。此后一段时间,王之碧经常调侃黄天雪“意志避孕法”的破产。三十多年后我重返显周,见到黄天雪,又像当年一样调侃起“意志避孕法”来,黄天雪说:“怎么,你还记得呀?”我们相视大笑。
第二章 新的生活
【1】门框上倒挂着一条蛇!
日子在百无聊赖中一天天过去。
我住在那个弥漫着毒气的小土屋里,日日忍受着毒气熏蒸,忍不住又向拔山区供销社提出了把小屋和农药库房之间的格子窗封闭起来的要求。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钱主任没有再说什么,竟然痛痛快快地同意了。于是请来工匠,把空格用木条钉严,再抹上石灰。这样毒气就大大减少,只是原先小屋经多年毒气弥漫,已经熏透了每一寸墙壁,完全无法清除,也只有忍受了。
大约三个月后,又有了一件好事:显周场通电了。我的小土屋里也挂上了一个小灯泡。按照规定,只能使用15瓦的灯泡,由于是从小电站引来的电源,电压不稳,灯光非常微弱,但是从煤油灯到电灯,总算跨越了一个时代。从16岁插队落户当知青开始,我就与煤油灯为伴,从此永远扔掉了煤油灯。
屋顶的瓦片底面经岁月积累,早已悬挂满了灰尘,时不时会掉到头上来,瓦缝里还长着一种浑身是刺的毛毛虫,不小心掉到脖子上,会马上让皮肤起大块大块的疱疹,既痒又痛。
一次我从村上回到显周场,正跨进房门,忽听得头顶上呼呼作响。我回头一看,门框上方刚安不久的横向电灯线上,竟倒挂着一条蛇!蛇长约三尺,全身黑褐色,长着细小的黄色花纹,蛇头向下,吐着细长的舌头。我的门本来就很窄,蛇从上面垂下,悬在门的正中。我如果冲出去,蛇头会碰着我的头。没有退路了,怎么办?
我从小最害怕蛇,蛇既恐怖又恶心,说到蛇我就会条件反射一般心惊肉跳。可是此时我却被蛇挡在一个狭小的死角里无路可逃,我感到心跳加速,额头有细小的汗珠冒出。
我呆在原地和那蛇对视了一会,看样子它没有离开的意思,还缠绕在电线上向下悬挂着,头微微地左右摆动。
不能老是这样呆着,我不能一直被它挡在屋里,不除掉它,它就可能伤害我。必须尽快打破这种僵局。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只能自己解救自己了。我壮起胆子环顾身边,竟没有一样可以作为武器的东西,于是心中又有些慌张,总不能赤手空拳去对付那丑陋的东西吧。好了,墙角有一个扫帚,扫帚毛快掉光了,只剩下一个结结实实的扫帚疙瘩,别无选择,就权且用做武器了。
我抄起扫帚站直身子深吸一口气走到门下,跳起来猛的一下朝那蛇打去。谁知它只是稍稍摆动了一下,照样悬挂在那里。我告诉自己别心慌,沉住气,使足劲再狠狠一击。这下那家伙应声掉下,软软地落到地上。我赶紧用坚硬的扫帚疙瘩拼命打它的头,一边打,一边心里却跳得咚咚响。那家伙被打昏了,身子痛苦地痉挛着,我乘势一脚踩到它头上,坚硬的皮鞋后跟在它头上反复碾压。它的头慢慢被压扁直至破碎,细长的尾巴在地上扭动几次后,终于一动不动。它死了!
我用扫帚小心地把死蛇挑起走出门去,往断崖边远远地抛出去,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然后那家伙就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险情到此结束,一个最怕蛇的人独自打死了一条蛇。人被逼到没有退路的时候是会激发出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勇气的。很多人之所以缺乏勇气,不过是因为还没有被逼上绝路而已。我出了一口大气,心里升起一种胜利的喜悦,畅快极了。
那以后,我在小土屋里又先后两次遭遇蛇,而且都是晚上。一次,一条蛇横卧在我床前的布鞋上,与布鞋垂直相叠;另一次,一条蛇盘在床下,圆圆的一堆。我有了前次的经验,都取得了打蛇的胜利。勇气是逼出来的,胆子是练出来的,后来我再也不怕蛇了。
【2】并非爱情的故事
公社已经决定由我蹲点大云大队,因为那里的棉花种植面积比较大。大云1队和2队分别种有15亩棉花,与之相邻的老龙3队也有15亩棉花,连起来是45亩,算全公社最大的一片。我到那里正好督促这一片的工作。
我哪里懂棉花生产,情急之下,赶紧找些资料来看,才知道了一些浅显的知识,什么洞庭棉、鄂光棉,什么打枝、治虫。其实川东气候根本不适合种棉花,就像不适合种双季稻一样,不知道是那个官员头脑发热,把种棉花当成政治任务来强制推广。在中国,只要是政治任务,就不需要考虑科学性了。
我其实是很能吃苦的,在大云大队,我还主动参加棉田的劳动。我1973年6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独自到大云1队,正值棉花管理组在挑粪水施化肥,于是我找来扁担,挑起粪桶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姚队长叫我自己休息,我仍然坚持一起劳动到中午收工。中午在姚队长家吃饭。姚队长是个女同志,担任着公社革委委员、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长的职务,在社员中很有威信。下午4点后离开1队,去各队查看了一遍,6点后返回了公社。”从中可见我工作之一斑。
我的直接下级是大云大队的副业大队长黄益清。黄益清,40多岁,光头,皮肤黑中透黄,个子瘦削,不爱言语,是个很忠厚的人,他家住大云4队,也就是黄天雪老师那个队。
黄益清夫妇二人只有一个女儿,一家三人和和睦睦。女儿叫黄新琴,大约十八九岁,梳着两条乌黑的长辫子,面目姣好,清秀可人。和农村一般女孩不同的是,她没有多少土气,似乎还有一点儿城市女孩的气质,言谈举止也比较得体。那时农村很多青年是不刷牙的,而她却天天刷牙,有着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她的与众不同,使我有些好奇。交谈之余,才知道她有亲戚在川北旺苍一带,她曾经在那里的城市里生活过,这在当时的农村女孩中是不多见的,那时显周公社绝大多数女孩终其一生的活动半径都很难超过50里。
我每次到黄益清家,都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晚上他们会把黄新琴的闺房让出来给我住。黄新琴的闺房收拾得整齐干净,里面居然有爽身粉之类的用品,这在农村是绝无仅有的。
按理说,我和黄新琴之间就会发生点儿什么爱情之类的故事了。可是,竟然一点儿也没有。这是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在农村安家,从来没有考虑过谈恋爱之类的事情。同时,黄新琴是个很含蓄的女孩,很少和我交言,更不会表露一点与情感有关的言行。
但是,由于我在他们家进出的时间多了,一些热心的人硬是给我们弄出些传闻来。
大云2 队的副队长袁林珍,是个50左右的大妈。她儿子毛昌杰是正在服役的海军战士,儿媳叫陈文朴,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我在查看生产情况时去过她们家多次,因为陈文朴和我都姓陈,我和她们家关系就比较好。在她们家,我第一次看到了美丽的珊瑚和海石花,那是陈文朴去海军部队探亲时带回来的,玲珑剔透,光洁莹白,珍奇无比。袁林珍大妈出于对我的关心,看到我单身一人,主动提出要给我做媒。我委婉地拒绝了她。她可能以为我是不好意思吧,还是坚持要做媒。
袁林珍大妈给我介绍谁呢?黄新琴!
我想她一定同时也给黄家说过了,或许黄家也有那么点意思。总之这话就慢慢传开了。忠县后乡的风俗,是把男女双方谈朋友称为“订婚”,于是甚至有人说我已经和黄新琴订婚了。不过,这些传闻还没有传到我耳朵来,我还照样在下村时到黄家去,因为和副业大队长联系是我的本职工作。
这一天,潘经理很严肃地找我谈话。他叉着腰,眼睛非常专注地望着我,嘴唇紧闭着。看样子是在考虑如何措辞。半晌,他清了清嗓子,从喉咙发出短促的哼哼声,说:“老陈,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他又犹豫了一阵才终于说出“有人反映你订婚了。有这回事吗?”
我脑袋猛一下嗡嗡直响,那时谈恋爱一般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有些害怕别人说我有资产阶级思想,就赶紧分辩,说:“没有没有!”
“你要说老实话,如果有,要对组织上说清楚。如果没有,我心里也才有底。”潘经理说。
我说确实没有订什么婚,都是人们瞎说的。
潘经理还在继续问我:“是不是真的对黄新琴没有那种意思?”
我说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为了让潘经理相信,我说:“我早在城里订婚了。”
潘经理说:“真是那样,我就给他们说,你已经在城里订婚了。”
谈话就这样结束。从此我很少去黄益清家,慢慢的,人们也不再说这件事。但是我对黄新琴的印象还是较好,我从心里祝福她。
多年后,我已经调返县城,也有妻小了,一次因公到拔山出差,偶然见到了挑着担子来赶场的黄益清,我把他请到饭馆里,举杯敬酒,对他一家当年给予我的照顾表示诚挚感谢。并询问黄新琴的情况,黄益清说,黄新琴早已结婚生子,丈夫是煤厂工人。那时农村姑娘能够嫁一个工人就算很幸福了,可以想象黄新琴的日子还是比一般农村姑娘过得好。黄益清回忆往事,淡淡地说:“那年都怪袁林珍多事。”
【3】宣传推广土农药
种棉的农民普遍反映缺少农药,棉蚜虫棉铃虫和金刚钻什么的,治不了。特别是金刚钻,钻进棉桃里去危害,简直没有办法。当时物资奇缺,常用的农药只有乐果、223乳剂(DDT)、666粉剂等,对棉虫没有特效。这时上面的办法出来了,号召大家熬制土农药治虫。我每天游走在田边地角,就反复宣传土农药治虫的好处。
县上统一印发了大幅的彩色宣传画,用醒目的大字印着,“土农药治虫,费省效宏”,宣传资料上写着当时的套话:“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历来反对贫下中农用土农药治虫,要深入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肃清他在土农药方面的流毒”云云。真不知道这是哪跟哪。
土农药主要有这样一些:石硫合剂,就是把石灰和少量硫磺混在一起做成合剂。八合一,就是把桉树叶等八种树叶合在一起熬制成药液。最奇特的是水牛尿治虫,将水牛尿集中发酵至一定程度,就可以盛入喷雾器当农药使用。为了推广这一“科技成果”,万县地区在忠县新生公社召开了九县一市的现场会。万县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一个主任在会上作报告,说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求我们会后回到公社,给每头水牛用塑料做一个兜把牛尿接起来,按照每头牛每天三泡尿计算,除去抛洒多少,还剩多少,每年应该生产水牛尿农药多少……当时各县代表都在会上发言表态,回去就要给水牛做兜等等。还有的人谈自己的认识,说:“尿开始拉出来一点不臭,在夜壶里装几天就臭得很,那就是发酵的作用。水牛尿经过发酵可以当农药用,就是这个道理。”不知道那些人回去后如何,反正我们是没有给水牛做兜的。
老龙5队是当时制作土农药的典型,拔山区供销社指令我写一个简报在全区推广,我为此到老龙5队走访了生产队长邱景安(他后来提升为大队书记)。
邱景安住在龙桥附近的一个小院里。龙桥是一座石平桥,架设在一条小河上,我估计小河的源头之一就是流过显周场的那条小溪。这是一条非常美丽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可以清楚地看见水中一寸两寸的游鱼。河道婉转悠长,在相对宽阔的谷地上绕来绕去,形成多个S形。小河两岸是两排茂密的竹林,像两道绿色长廊,把绿荫投向清清的河水,守护着婉转的河道。龙桥桥头竖立着一块约五尺高的石碑,碑顶大书“幸福桥”三字,碑文略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特将龙桥改名为幸福桥。”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见有人叫过幸福桥,都是叫龙桥。
正是端午后不久,天气开始炎热,我在龙桥旁找到了邱景安。
30多岁的邱景安是农村中比较能干的人,他对我很热情,吩咐老婆给我“烧茶”。“烧茶”是忠县后乡的淳朴民风,客人到了,先“烧茶”招待。所谓烧茶,实际与茶毫无关系,一般说来,烧茶就是给客人煮一碗汤圆,或者煮两个醪糟蛋。我第一次享受“烧茶”待遇时搞得莫名其妙,怎么不见茶呀?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民风几乎不能再坚持下去,只有比较优裕的家庭才能给客人“烧茶”了。邱景安家就属于这种。
在邱景安家的桌子上摆着一台当时堪称奢侈品的“三唱机”,“ 三唱机”是兼有收音、播音、放唱片三种功能的一种音响设备,别说是农村,就是城里也不多见。这是生产队的公共财产,因为老龙5队条件较好,才购有此种设备。邱景安可以坐在家里对着“三唱机”向全生产队社员发号施令:“今天上坡挖红苕”,或者放一曲“临行喝妈一碗酒”,非常惬意的。
我向邱景安详细了解他们生产队制造土农药的先进事迹。
邱景安说,去供销社买不到农药,急死人,没有办法,就自己熬八合一。熬好后拿去李子树上试用,那时李子树刚刚结果,长满了“天蝇”(即蚜虫)。“天蝇”黑麻麻的把鲜嫩的李子裹了一层,很讨厌。把八合一装进喷雾器对着李子喷洒,眼看着“天蝇”就一片片地掉了。大家都说,嘿,土农药还真行。后来就大量熬制使用土农药了。
我把邱景安的经验写成简报后复写几份,分别送县供销社、区供销社、显周公社等。在简报里,我照例写了“深入批判刘少奇”云云,还特别突出了当时高喊的口号“人定胜天”。简报在区供销社颇获好评,谢宝鉴会计向我伸出大拇指连声说:“你这个本事今后有大用”。
【4】显周场上的“疯景”
显周场上也偶尔有意想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最荒唐的时代,往往容易产生疯子,换言之,疯子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由于疯子不同于常人的举动,不论他们出现在哪里,都能迅速成为最吸引人的“疯景”,引起满场大笑。中国人的喜欢围观和疯子相结合,总能造成轰动。
我多次看到一个疯女人在公社门前的台子上跳舞。说是跳舞实在是亵渎了跳舞两个字,那种扭来扭去的丑态令人作呕。但是,偏偏是这种丑态却特别引人注目,台下不时爆出哄笑声。
那个疯女人已经年过半百,脸色苍白皱纹密布牙齿脱落。她时而仰天狂笑,时而掩面痛哭,灰白肮脏的头发像乱草飘动,破旧的长衫像揉皱的废纸一样抖摆。在围观者的大笑声中,她像变戏法一样从怀里掏出一把残缺的暗淡无光的口琴放进嘴里,稀里呼噜地一阵瞎吹,随着怪怪的琴声,她从台子的这边扭到那边,又从那边跳过来,所到之处灰尘扑腾,笑声四起。
有一次,当疯女人正跳得起劲时,一个表情严肃的40左右的男子上前制止。这男子体形敦实,眼角下斜,脸色铁青,穿着灰色的中山服,他是公社武装部长张明楷。张明楷挥着手,叫疯女人离开公社大门。那疯女人回头眯着眼睛把张明楷上下看了又看,嘴里发出长长的嘘声,然后把脸凑上去唾沫飞溅地说:“你们这些公社干部,天天开会,天天吃好的。”搞得张明楷一时回不过神来。这时疯女人忽然扯开裤裆大叫:“张部长,我这里有两块臭麻B,你吃不吃?”张明楷铁青的脸一下变成紫色。那疯女人却提好裤裆,若无其事地把口琴横放在嘴里,吹着依依呀呀的声调飘然而去。
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正当疯女人舞动得有些乏味时,一个约20岁的小伙子走上台子,也随着怪怪的口琴声乱舞起来。那疯女人像找到了知音似的,腾出一支手来捉住小伙子共舞。
“田洪亮!”台下有人叫。
小伙子除了痴痴地笑莫名其妙地乱舞显得有些不正常外,其实还算是一个很端正的青年,他浓眉大眼高鼻梁国字脸,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草绿色军装,有着山乡里人少有的那种书生气,可惜,这小伙子也是个疯子。
疯女人有了小伙子做搭档,疯得更起劲,台子上下顿时高潮迭起。
在这个偏僻寂寞的山区小乡场里,似乎只有这时人们才忘记了忧愁开怀大笑。
我后来才听说了疯女人的一些故事。她姓陈,天堡大队人,她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她老公叫欧天和,所以都习惯叫她“欧天和屋的个(家里的)”。她已经疯了多年,每天疯疯癫癫又说又唱。老公欧天和忙着学大寨,穷得买不起盐,哪有钱给她治病,她的病就一天天严重了。说来也巧,那时正好人和大队也有个疯子,叫王心良,他俩居然心心相印,发生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真正疯狂的爱情。疯女人没事就跑到人和大队去找王心良,疯子遇到癫子,真是爱得死去活来,情之所至,还一起到溪河里去共同裸浴,踏沙戏水,嬉笑自如,破了山乡里男女不能共浴的老规矩。发展到最后,甚至手牵着手到公社去领结婚证,公社当然不会同意,而他们就认为已经办好结婚手续了,回头疯女人就带着王心良到自己家里,两人挑走了两大挑谷子,说是拿去办喜事。那时粮食非常紧张,欧天和得知后,追了几道湾才把他们拦住。当气喘吁吁的欧天和要王心良放下谷子时,疯女人挺身而出挡住欧天和,振振有辞地说:“你要做啥子,我们是扯了结婚证的!”
王心良的经典故事也不少。一次他去拔山赶场,遇上区里开大会,有20多桌人吃饭,每桌配有一碟豆腐乳。吃饭结束后桌上还残留着许多豆腐乳,有人对王心良说,那豆腐乳是好东西呢,吃吧。他尝了尝还真有味,就把一碟豆腐乳吃完了。人们就鼓励他说,有本事干脆把20多桌都吃了。王心良傻傻地笑了笑,真的一桌桌挨着吃,全吃了。豆腐乳很咸,他一下吃了那么多,胃翻起来渴得要命,在回家的路上,王心良见到水田就趴下去捧水喝,一路喝起走,把肚子都灌得亮晶晶的。
后来,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给王心良开了个更大的玩笑,他指着一瓶农药对王心良说:“你敢不敢喝这个?”王心良傻乎乎地笑了笑,打开瓶子就一阵猛喝,这下就玩完了,一会儿王心良就抱着肚子惨叫,倒下地翻白眼吐白沫打滚抽筋,死了。
王心良死后,疯女人披头散发呼天抢地地大哭一场,从此更疯了,每到赶场天就去公社门前的石台上乱跳乱唱,后来又不知从哪里捡来了一把烂口琴,有事无事都乱吹一通。
农村里谁会有口琴呢,原来这口琴是重庆下乡知青田洪亮带来的。
田洪亮是重庆南岸下乡到天堡大队的知青,长得浓眉大眼壮壮实实的,外号叫“肥人”。他在农村劳动很积极,村上都说他是个好青年,可是由于家庭情况较差,他一直无法调回重庆。眼看着身边的知哥知妹都一个个远走高飞,久而久之他便对生活绝望了,从重庆带来的口琴开始还可以给他解除一点寂寞,后来他心生厌倦,把口琴也摔破了。这口琴竟被同村的疯女人捡去当成了宝贝,带在身上随时摸出来乱吹。田洪亮最后终于精神失常,间歇性发作,成了老疯女人的搭档,招来满街大笑。病态发作时,田洪亮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旦清醒过来,就伤心不已。
县上知道了田洪亮的情况,送他去县精神病院治疗,但此时病情已经严重,于是又转到重庆治疗。在重庆,田洪亮发病时挥刀砍下自己左手的手指放进嘴里吃了,吃得满嘴鲜血,然后又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清醒后他痛不欲生,跳进长江自杀了。
田洪亮的父亲到显周来清理遗物,我看见那个愁容满面的男子失魂落魄地徘徊在显周场上,揹着一口旧木箱,木箱上横搁着一卷陈旧的竹席,那是他儿子一生的全部遗产。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