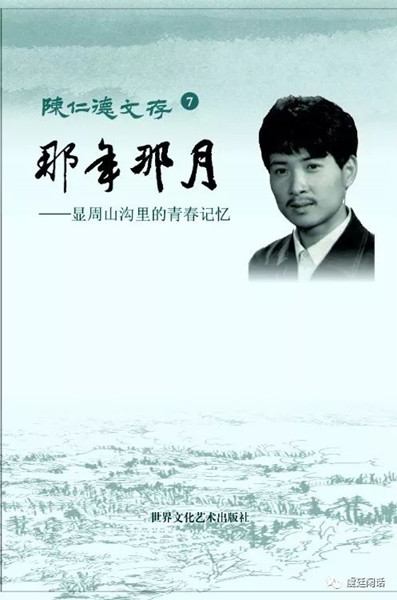
【4】“搞工作怕臭,行吗?”
第二天,潘经理带我看了另外安排的寝室。由于有了前一天的经历,两相比较,我得承认,这间寝室虽然十分寒碜,却要比食品门市楼上好得多。
这是靠着副食门市部背后的屋檐续建的一间小“偏偏”土屋,面积不到10平方米。房屋最高的一边就是副食门市后檐,两米多高,最低的一边不到两米,伸手可以摸到屋顶。屋顶没有天花板,一片片陈年青瓦历历在目,瓦片上悬挂着蜘蛛网和灰蒙蒙的积尘。低墙上开了一孔约一尺五见方的窗口,窗口是几块竖着的木条,光线就从木条间透进来。房屋三壁都是粗糙的土墙,大大小小的裂缝像沟壑一样,最深的裂缝穿透了墙壁,可以看到外面透进的光线。房屋的另一壁却是木格子,每个格子七寸见方,差不多可以把头伸进去。从格子望过去就是生产资料门市部的仓库,也就是生产资料门市部的背后。仓库里堆放着农药农具,浓烈的农药味毫无遮挡地弥漫到房屋里来。
靠着窗口是一张长方形的陈旧的从未刷过漆的小木桌,上面有一个用废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显周公社至今还没有通电,照明依然靠油灯。桌面上有一大片亮晃晃的东西,居然是一块玻板。走近看全是破碎的,最小的碎片只有指头大,最大的一块有巴掌大,在破碎特别厉害的部位贴着一条条的胶布,已经没有了粘性的胶布一条条地卷了起来。
小木桌前没有凳子,如果要坐着写字,真还不知道怎么办?
小木桌左侧是一张空空的木床,不要说床板,就连“篾巴笮”都没有。
我别无选择了,只能在这里住下来,而且不知道要住多久,也许是一辈子!
带着莫名的惆怅,我走出小土屋,在外面徘徊良久。小土屋窗外是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土坝子,上面长着稀稀疏疏的杂草和零乱的竹树。土坝子的边缘是一道二三十米高的断崖,断崖旁有一条仅容一人的小道斜着通向崖底。我顺着小道走到崖底,却是一个很幽静的地方,从显周戏楼那里流下来的溪水流过两道高崖后,在这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瀑布,瀑布的水量不是很大,但是却飞珠溅玉叮咚作响声如弹琴。瀑布背后是一个洞口,堆积着嶙峋嵯峨的钟乳石,那些珠玉般的流水就终年冲刷在钟乳石上。后来我才知道,老乡们之所以世代相传,把显周叫卷洞,就是因为这个洞子的原因。
溪水跌落下洞口后成扇面铺开,浅浅的溪流散成无数条粗细不均的线条,从一大片凹凸不平却很光滑的青石上流过,小溪两边全是苍翠欲滴的竹树,掩映着湿润的青石。在近岸的地方,青石忽然下陷成一个天然的圆井,那简直是一个标准的360度的圆形,直径约四尺,深约三尺,中间盈满了清清的溪水,我想,月明之夜,当月光正好映到这里时,该是何等美丽,从此我就叫这个地方月亮井。
我向潘经理反映了我寝室的一些问题,比如需要粉刷一下墙壁,需要一个凳子,通往农药仓库的格子墙壁应该封闭以隔离毒气等等。潘经理立马就去请来了钱主任,他不是正好在显周吗。
2014年7月24日,作者回到显周,当年故居犹在,只是土墙“提档升级”翻新成了石墙,而基本格局依旧。
我向钱主任谈了我的请求,我特别说了农药仓库里的毒气可能对我身体造成毒害。钱主任开始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就有些不耐烦了,他在窄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高大的身躯在矮小的房间里显得有些直不起来。他把头偏过去狠狠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半晌不说话。潘经理在旁边已经有些紧张了。
“闻臭?农药臭?哪个不闻臭?周胡子不闻臭吗?他闻几十年了,从来没有说过要毒害身体。”钱主任猛地把烟头丢到地上,用脚踩了又踩,大声说:“搞工作怕臭?行吗!”
我一下惶惶无主,无言以对。
他说的“周胡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周胡子”叫周广衢,是拔山区供销社生产资料仓库保管员,的确是接触了农药毒气几十年,也的确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毒害身体。可是……可是我的确害怕毒气呀!
钱主任一直侧面对着我,没有正眼看我一眼。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着。临走时他丢下一句话:“写个报告来我们研究。”
我随后请潘经理写了报告,要求添置木凳子,粉刷墙壁,封闭格子窗等,总共需要10元,请区供销社批准开支。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特点,用一分钱都得给区社写报告造计划,分社没有自主权。
几天后,我去拔山区供销社向钱主任面交《报告》,他当即批复,同意添置木凳子一个,其余一概不予批准。
回到显周,我添置了木凳子,找来了一块“篾巴笮”铺床,去潘经理那里找了许多废报纸,将寝室四面都糊上了报纸,又把破碎的玻板小心擦拭干净,在最大的一块玻璃下压上我的几张黑白照片,把堂兄俊德画的两幅紫藤八哥挂在墙上,屋里顿时焕然一新。只是农药的毒气却无法消除,只有忍受了。
【5】 跟着潘经理下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潘经理带着我走遍全公社12个大队,去了解公社多种经营的基本情况。
所谓多种经营,是指的在粮食作物生产之外的多种经济作物生产,这些经济作物主要是由供销社收购经营,每个供销分社都配有一个多种经营员,又叫多种经营干部。在公社下面,每个大队又配有一个副业大队长负责多种经营生产,由公社多种经营员直接管理。副业大队长每月由供销社发给每人2.5元到3元不等的工资,显周公社共有12个大队,由我按月分发工资。不要小看2.5元到3元,这可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待遇,副业大队长们每月都会很恭敬地到我那里来签字领取。直到现在,已经40年了,我还记得12个副业大队长的名字。他们是:人和大队王兴同、大云大队黄益清、老龙大队余朝寿、师联大队王顺和、天堡大队刘家培、鱼箭大队顔光普、天井大队杨世英、沥石大队潘全槐、前进大队张清奎、安乐大队刘学培、老鹰大队李正谷、中苏大队袁世槐。
多种经营在名义上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其品种包括“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这12字中前11字都是具体的经济作物,第12字“杂”泛指其余所有的经济作物。事实上当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一切都为粮食让路,经济作物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显周公社的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和毛烟,共有两三百亩。我到显周正是棉花打枝治虫、毛烟加强田间管理的时候。潘经理带着我迂回穿插在各个村落,给我介绍各个村的情况。整天奔走总会令人疲倦,但是潘经理却精神抖擞,说他一二十年来见过很多大场合,创造过很多业绩,除了依然要说到“曾经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在保险公司秘书处工作过”之外,还说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供销社的所有业务他都精通,几个门市部的工作他一个人就能够胜任。“公社党委给我的担子太重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信任我,知道只有我才行。”
潘经理可能是有鼻炎还是什么,鼻涕很多,过一会就要捏住鼻子呼呼地擤一通,把粘糊糊的鼻涕顺手一甩,然后俯下身去把手中剩余的鼻涕擦在路边绿油油的烟叶上。当我还在惊讶时,他已经平静地站起来,继续说:“那年我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他这一独特的动作,也就不以为然了。他在下队时都是把鼻涕擦在路边的烟叶或者菜叶上,如果是在显周街上,没有了烟叶菜叶,他也有办法,他一边和你谈话,一边擤鼻涕,然后转身把鼻涕慢慢擦到墙上,两个指头翻来覆去很从容地往墙上擦。擦完了继续谈话。
在我几十年来认识的各种人物中,潘经理还算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显周街上每次见到他,总是在匆匆行走,背向前倾,像要俯冲的样子,两手大幅度前后摆动,显得非常忙碌,所以人们背后都叫他“无事忙”。他虽然手下一共只有几个兵,但还真有一点当官的风度。假如你找他谈点什么,他会立即挺起向前倾斜的腰身,把双手叉在腰间,很严肃地望着你,使劲清一下嗓子,再“嗯”一声,表示你可以说话了。如果你的话出乎他的意料甚或让他感到不好办,他就会作深思状,让双肩向左右轻轻地来回扭动,而眼睛却一直望着你。当然,他这时也会擤鼻涕……
跟着潘经理下队这段时间,可以从我1973年5月22日的日记中窥见一斑:“今天开始下队了。潘经理决定带着我去全公社巡视一週,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再由我独立工作。早晨天又下起小雨来,饭后我们从场上出发,由于有雨,我们都带上了雨具,我披着森哥(家兄储德乳名森森)的雨衣。谁知一会儿就没有下雨了,我只得抱着雨衣走。路很滑,我们经过人和大队、鱼箭大队,到了中苏大队,这是全县有名的典型大队。后来又去了天井、前进,下午2点钟在老鹰三队王队长家吃午饭。饭后又到了沥石、在沥石参加大队干部会。今天共走了七个大队,与各大队副业大队长见了面,逐块检查了棉花以及毛烟、蚕桑、甘蔗等。棉花普遍长势比较可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缺窝、草多、生虫等。种棉人员一致反映肥料紧缺。我们向他们做了鼓动工作,要求他们赶紧把补苗保苗工作搞起来。缺肥可以积肥,生虫可以熬土农药治。晚上在沥石代销员萧显发家食宿。这个队是潘经理亲自抓的典型,今天(晚上)开会到12点才结束。”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我们连续走了七个大队,而且是在“路很滑”的情况下,手中抱着厚重的帆布雨衣前行。七个大队分布在不同的方位,并不是在一条线路上,我们必须时而登山,时而过河,为了“逐块检查”棉花毛烟等作物,为了寻访各个大队副业大队长,还必须迂回绕行很多路程。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开会到12点”,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6】赶场的日子很热闹
除了下队指导多种经营生产,潘经理还要我把收购门市部一直由韩家虎担任的付款工作接过来。我每逢赶场就到收购门市部去付款,那里有一张小桌子供我使用。收购门市部伯有训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开玩笑说“荤话”,但有时却很有锋芒。我很快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到逢场的日子,我就提着装满现金的小箱子坐在他对面的桌子后面,他收购了物品,开一张票,出售者就凭票到我手里取钱。收购的物品多为农副产品,比如草袋、牛绳、烟叶、半夏等。那时毛猪收购也是供销社的业务,也由我付款。于是兽医站的站长黄启尧找到我,请我为他代收毛猪保健费,只要卖了肥猪在我这里领款的人,按照每头猪0.50元的标准交保健费。我痛快地答应了。兽医站按规定收费,一般都收不到,在我这里则完全可以卡住了。
我付款用的现金由我去拔山区供销社开具现金支票,去农行拔山区营业所取回,每次几千元,遇到节日杀猪最多可取一万元。一万元是个很大的数字,等于我当时30年工资的总和。我每次带着现金都是独自步行回显周,根本没有想到抢劫什么的。
不论多么偏远的山区,到了赶场的日子都是很热闹的。山民们把赶场视为生活中的乐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一生见过的最大场面就是赶场。一般说来,很多人一生的活动半径都不会超过50里,因此对于赶场是很看重的。他们从各个方向来到场上,见面后互相打着招呼,甚至说着戏谑的话,有说有笑。显周的风俗不论男女都习惯头上包着帕子,揹着方形的小背篼,虽然那些年月大家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从他们赶场时的快乐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收购门市部里经常挤满了山民,有时卖草袋和牛绳的人排成了队。山区里的小孩都会编织草袋,他们家家都有一个用来编织草袋的机器——其实就是个木架子,选出比较长的稻草先搓成“经”,一根根竖挂在木架子上,再把“纬”——一根根稻草横着织进去——当然实际操作没有这么简单。看上去是在编织一张平面的东西,可是编织出的口袋并非平面,而是中空的草袋。草袋约两尺宽三尺长,专门用于装过磷酸钙一类比较粗重的化肥。山区的男人都会绞牛绳,把竹子剖成极薄的竹片,再绞成绳子用于牛耕。这些东西外地的需求量较大,我们收满一车就马上外运。
我到显周不几天就是农历端午节,这一天本来不赶场,可是山民们却纷纷来到场上,比赶场还热闹。据说代代相传的风俗就是,只要遇到传统的节日,不论是否场期都得赶场。这一天还是山里的青年男女们相亲或者看望未来岳父母的日子,他们都尽可能地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先到场上风风光光地走一趟,再到对方家里去。村姑们脸上挂着朴实的笑容,没有半点的矫饰做作,她们虽然穿着十分朴素甚至粗陋的衣服,可是青春的气息却掩饰不住地向外迸发,那种清纯,那种阳光,是只属于山区村姑的。这时桃子刚好成熟,于是村姑们随身的布袋里带着鲜嫩的桃子,见到相熟的人,就掏出来热情地递过去。略带青涩的桃子采下来时往往还连着绿色的叶子,清脆鲜嫩,咬起来咯咯有声,感觉好极了。初到显周的我,成了小小乡场上的陌生人,赶场的人们尤其是村姑们不时会把目光投向我,个别勇敢的村姑会走过来热情地请我品尝新鲜桃子。我突然感悟到,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否贫困,只要你热爱生活并善于发现美,生活就是美好的。
【7】我其实还是一个孤独的“知青”
我在显周场上的出现绝对是十分吸引眼球的,那时我刚结束知青生活,还是一副十足的知青模样,紧身的海魂衫扎在皮带里,下穿米黄色的筒裤,脚上是从重庆买回的接尖皮鞋,英武挺拔,潇洒自如,在偏僻的显周场上算是惟一的异类,谁都可以在众多的人群里一眼把我分辨出来。因此没有多久就传开了——公社(机关)来了个知青。
城里的父母知道后很关心我的形象问题,担心被说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再来信告诫我要艰苦朴素。于是我开始努力改变形象。我穿上父亲从城里特地给我寄来的一件粗蓝布的中式对襟衣,下摆长长的;脱掉接尖皮鞋,赤脚下村。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让饱受极左摧残的父母暂时放下了悬着的心,而我却受苦了。每天赤脚下村,坎坷粗粝砺的山路把脚掌磨得难受,最可怕的是炎热的夏天里,山坡上的石板被晒得发烫,干裂粗硬的田埂像刀子一般,赤脚踩上去生痛。这些我都忍受了,在此之前的知青时代下地劳动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说得更早一些,我从童年到少年有几天穿过鞋呢?不都是赤脚吗!
形象的改变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公社官员们和山民们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改变,而且我不论在哪里出现,和山民们一比,依然有点儿“资产阶级”的样子,真是无可奈何。后来我就不管那么多了,该怎么就怎么,管得别人怎么说。
除了山民外,显周公社的知青们也关注到了我,他们显然也发现了我这个异类。那时全公社有将近100名重庆下乡知青,年龄都和我相仿佛,基本都是和我同时插队到农村的,只是我现在的身份变成了多种经营员而已。我很快就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
知青每逢赶场必然到显周来,一是看有没有家中的来信,二是和同学相聚。在那些寂寞枯燥的日子里,这些时代弃儿最开心的日子就是赶场。
显周场有一个邮政代办所,设在人和大队副书记韩国政家里,那里是知青聚集的中心。韩国政家里和所有农家没有区别,灰暗邋遢,门前堆着柴草。不同的是门上挂着一块两尺见方的已经明显褪色的黑板,上面由韩国政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着“电报,汇款,挂号……”以及一串名字。在屋里黑糊糊的木桌上,乱七糟八地堆着一大堆平信。韩国政戴着一顶邮局特有的帽子、衔着一根短烟杆坐在木桌后面,脸色苍白,面容凝重,不苟言笑,眼神威严。有人问:“有没有我的信?”他并不回答,只是把衔着烟杆的嘴往堆着平信的桌子方向翘一下,意思是,在那里,自己看。
来到邮政所的知青以最快速度扫视完门前的小黑板,接着是翻检桌子上的平信,如果见到家中的来信或者汇款,就激动万分,反之则心灰意冷。
电报其实也是用平信的方式传递,先由忠县邮局将收到的电报内容用电话告知拔山邮局,拔山邮局记录填写在电报专用纸上,送到显周韩国政家,就堆在那里,一直等到有一天被收件人偶然发现。
我虽然离家只有一百多里路,可是就像隔着万水千山似的,孤单一人,寂寞难耐,每时每刻都想念着父母亲人,两三月都难得有一次机会回城。那时中国已经反复批判过家庭观念,要求人们树立“社会主义大家庭”观念,想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我和家里的联系,也是靠信件,所以,韩国政那里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可能是全公社私信最多的人,三天五天准能收到来信。拆阅来信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每封来信我都要反复读多次,差不多能够背诵。给我来信的主要是父母、兄弟、亲戚和外地的同学。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喜爱写信的人,他给儿女和外地亲友写信平均大约三天左右一封,他把所有发出的和收到的信都列表登记着,以备随时查考。父亲的这一习惯深深影响了我,我也对往来信件做了登记,记得最多时平均2.7天就有一封信。不论收到谁的信,我都会当天晚上伏在油灯下书写回信,从来不会等到第二天,因为,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我是把写信作为和亲人的对话,作为一种快乐来享受的。我只要铺开纸写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几个字后,就马上进入了一种境界,仿佛父母就在眼前。而搁笔之后,一切又回到了现实,昏暗的油灯,孤独的身影,低矮的土屋,窗外呜呜响起的阵阵山风,就不禁悲从中来。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