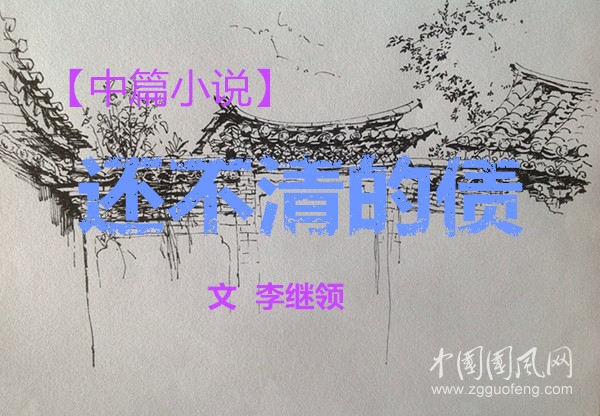
刘文革从城里打工回来,老婆不在家,他鼓起最后的勇气,坚定下意志,拿起了藏在门后边的一个农药瓶。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了,但是当他将农药瓶子放到嘴边的时候又迟疑下来。他想见老伴一面,和她句话再走。老婆的两个娘家兄弟为争夺她爹被汽车轧死而赔偿的五万块钱大打出手,差点出了人命。娘家一个旁门的亲戚过来找她去说理,她二话不说就走了……
刘文革拖着疲惫的身子骑电动车回到家,来到厨房想做点吃的,可是看看冰冷的灶台,想想他今天的遭遇以及近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顿时一股巨大的悲哀涌上心头,几滴眼泪便沿着面部的皱纹往下流。他觉得人活着除了吃苦受罪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今天,他早上天不亮就出去,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赶到县城,到城里时天刚透明。他来到城西关,这里有个自发的劳务市场:木工、瓦工、油漆工、杂工都在这里站着揽活干。虽然僧多粥少,有时几天等不到一个雇主,但这里必定存在希望,揽到一个活有时也能干好几天。只要有活干,一天也能挣到百把块钱。在这里等待揽活的大都是五六十岁的农民,他们有的为了照顾老人或孩子不能到外地去,有的因为年龄大了,没有什么技术,手脚又笨,包工头们不要他们,所以只能在这里碰运气,打零工。刘文革就是这种既没技术,也不灵巧,去不了外地的人。
他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偶尔见到一个雇主过来,大家便一拥而上,争抢着往上挤,盼望能被雇上,这时候当然有技术的优先。来一个雇主往那一站,一群人便争先恐后挤上去:
“老板,有啥活?我去。”
“老板要干啥的?”
“老板,我去!我是瓦工。”
“我去!我是木工。”
“我去!”
…….
那个雇主手一招说:“砌个灶台,要两个瓦工。”
于是几个手拿泥抹子的瓦工立即跳出人群围上去,眼巴巴望着那雇主争抢着说:
“我去!”
“我去!”
“我去!”
那雇主扫了他们一眼,“都别争抢,我想要谁就要谁,你们争抢也没用。”那雇主说罢就指着他们当中的某人说:“你一个,还有你一个。你们两个跟我走。”显然,在这里他们似乎没被当人看待,但是被点中者脸上却立即绽开灿烂的笑容,拎着工具就跟雇主走,没被点中的便垂头丧气,又退回人群中,然后接着东张西望,等待下一个雇主。
大半天过去了,来了两个要瓦工的,一个要木工的,一个要油漆工的,可是没有一个要杂工的。每来一个雇主,刘文革也都和其他人一起像饿狗看到了馍馍一起上去争抢,但是人家不要杂工,他就是拼命也没办法。近中午的时候,刘文革感到饥肠辘辘,冷风吹来,瑟瑟发抖,但他还是直冒虚汗。他犹豫再三,终于将手插进口袋里抠出一块钱硬币走到旁边的烧饼摊上买了两个大烧饼。他猛咬一口,然后慢慢咀嚼,真香啊!一个出体力劳动的男子汉,两只烧饼最多吃个半饱,或者说只够塞牙缝的,但是他强忍着没有再买,他要从牙缝里省钱。他出门时就想好了,身上只带一块钱,如果揽不到活就拿这一块钱买两只烧饼哄哄肚子算了;要是揽到活,东家自然给工钱,碰到好东家还会给饭吃。为大儿子结婚,他欠下十几万块钱的债要还,二儿子谈好对象就是没钱结婚,急死人啊!他没有能耐,挣不了大钱,又不能出远门打工挣钱,几亩地打下的粮食只够口粮,因此他必须从牙缝里抠钱。三毛、五毛、一块慢慢攒钱还账。这样,他家的粮食够吃的,喂个猪,养只羊,再卖几棵树,一年下来也能凑个一二万块钱去还债。
提起还债,更让刘文革悲愤不已,他是1966年出生的,所以父亲就跟着形势跑,给他取名叫文革。这也不稀罕,乡里人不会给孩子起名,总是碰到啥就是啥。所以五八年生的叫“跃进”;成立公社时出生的叫“公社”;初级社出生的叫“合作”;互助组出生的叫“互助”;六0年出生的就叫“狗饶”,那意思是没饿死去喂狗,是狗饶了他一条命。刘文革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了,不知怎么回事,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父母又生了他。听娘说,他出生的时候一身黄毛,瘦成一小把,落地时哭不出来,接生婆拎起他的腿摇晃,并照屁股连连拍打一阵子,他才“哇”一声哭出来,哭声凄厉嘶哑。父亲坚决要把他扔掉,或者放在尿盆里溺死。那时死了孩子用秆草捆上往乱坟岗子上一撂就完事了。可是母亲舍不得,对父亲哀求:“既生了就养着吧,养啥样是啥样。”
这样他就有幸活了下来,有了不是自己安排的人生。直到上小学的时候,在南山岗上还有个乱坟岗子,无论谁家的孩子死了,就用秆草一捆,往乱坟岗子上一撂,接着就有成群的野狗在那里争抢死孩子吃。狗群为争死孩子撕咬得狗血喷头,眼睛发绿。每次经过乱坟岗子,他就毛发倒竖,跟在大孩子后面拼命往前跑,扑通绊倒了,磕破膝盖,也不顾疼痛,立即爬起来还跑,直跑到看不见乱坟岗上的坟头了,才停下来喘口气。此时,他也在心里庆幸,自己没成为乱坟岗上的死孩子。那时生活虽然艰苦,可是他上面有哥哥和姐姐照着,比着别的孩子还算是好的。哥哥和姐姐的破衣服他可以穿,家里的杂活也不用他干,他除了上学就是玩。在早上背起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姐姐总是要往他的书包里放上一只煮熟的鸡蛋。姐姐常说:“由于条件限制,你哥和我没能上学,咱一家人供你一个上学,总是没问题的。就盼着你能上出来,有出息进城里找个工作,当个国家干部,全家人都能沾光。”
对姐姐的话,他似乎听懂了,其实什么也不懂,还是贪玩,整个小学都是在跑着玩,瞎胡闹。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国家突然恢复了高考,他才认识到学习的重要。于是他发奋努力,刻苦奋进,拼命学习,但怎么也赶不上人家,高中毕业一连三年参加高考都没考上。无奈之下,只得回家种地,由于他先天不足,身体瘦弱,种地当然没力气。那时候,种地全靠人力或者畜力,于是他就自然学会了使牛、犁地、耙地、播种、割麦等农活。读的书屁用没有,他后悔自己不该读了十几年的书,读的书没用上,干农活还不如人家一天学没上从小就学种地的文盲。
既然没考上学,父母就按老规矩给他盖了三间房子,娶了媳妇,然后让他分家另过。为了能把地种好,父母就帮他找个五大三粗又目不识丁的老婆。父亲对他说:“你身体弱,没力种地,总得找个身体强壮的媳妇和你一起劳动。要不然你将来咋过日子?”
既然考不上大学,他只能认命,听父母的安排,成家立业,过农民的日子。事实证明父母是对的,老婆既有力气又能干,像男人一样。几年后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虽然计划生育抓得紧,但在农村生两个孩也很正常。偷着生,躲着生,跑着生,或者买通计划生育干部开个准生证,明着生,反正办法总是有的。那时村上的年轻人好多因为没有儿子而发愁,他却一连生了俩儿子,真能让人羡慕死。然而没想到,后来正是因为这两个儿子才把他逼上喝农药自尽的绝路。
刘文革因为自己没能考上大学,因此就没能脱离这一片黄土地,他就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两个儿子相差不到两岁,从牙牙学语时,他就像城里的父母一样买些“看图识字”、“跟我数数”等低幼读物教孩子学习。无论多忙,无论干活多累,他不吃饭也要把两个孩子拉到跟前教他们学认字,掰着指头让他们学加减。这期间,他感到无限的幸福,儿子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欢乐。至此他才感到自己上了十几年的学总算有了点用,你看那目不识丁的家长就没法教孩子读书学习。两个孩子从小就培养起了学习兴趣,都很爱读书学习,上学后也都很用功,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更让他开心。当大孩子第一次拿着“三好学生证”向他报喜的时候,他欣喜若狂,一把将儿子抱起来,举到头顶,哈哈笑着说:“好儿子,真争气,爸爸要奖励你,奖你五块钱。”然后放下孩子就给老婆要五块钱递给儿子。老婆虽然不太情愿,但是看到丈夫和儿子都那么高兴,也觉得这是件大喜事,除了给儿子钱以外,又特意跑到集上割了两斤肉包饺子,庆祝这件大喜事。二儿子看到哥哥得了奖,当然也就加倍努力学习,于是弟兄两个学、比、赶、帮、超争着上进,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三名。这又不免引起亲戚邻居的夸赞,都说他家的祖坟埋得好,冒了青烟,生了这两个有出息的孩子。
孩子确实争气,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学习成绩都一直名列前茅,大儿子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大学,但嫌学校不好,又复习一年,第二年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并且都是国家的重点高校。这更让全家人高兴,让全村人羡慕,所有的亲戚邻居也都称赞不已。可是上万元的学费却让刘文革急得整夜睡不着觉,白天他在人前一副开心的样子,到了晚上头一挨枕头便唉声叹气。哥哥和姐姐听到了他为儿子上学的学费发愁,都积极主动地想办法帮助凑钱,你一千,他八百,在开学之前总算凑够了两个孩子的学费。这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可是从此就背上了一身债,不过农业逐渐实现了机械化,种地比以前省事多了,只要在下种和收割的季节里忙几天,剩下的时间就可以进城里去打工挣钱。在儿子上大学的那几年,刘文革正是壮年,没有什么技术,出笨力还是有人愿意要的。他儿子上大学的第二年,春节过后,他就跟着邻村的一个包工头跑到昆山一个建筑工地上去拎泥兜子。拎泥兜子是当地土话,意思就是给有技术的师傅打杂当下手,也就是干小工。那时大工干一天挣八十,小工一天能挣五十,大工干完活可以歇息,小工则没有闲着的时候,搬砖头、运水泥、筛砂子、拉石子,除了吃饭和睡觉,总是不能闲着的。
“出力不挣钱,挣钱不出力。”这正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刘文革为了能长期跟着包工头干,就尽力表现得更好些,凡事不用指使,该他干的活不用吩咐。在下雨天歇工的时候,他就去食堂帮忙,因为在食堂做饭的就是包工头的老婆。帮助包工头老婆干不要钱的义务工,当然让他们两口子都高兴,为此别人吃豆腐白菜、喝清汤,他却经常和包工头两口子一起吃红烧肉。他相信干活累不死人,多干活总没坏处。有时他扛着黄砂爬楼梯,累得头晕目眩,两眼直冒金星,但一想到儿子需要学费,欠人家的钱要还账,就咬牙坚持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我要干,我不能歇,等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都工作了,我就不再干这活见阎王的要命活了。
就这样,他一天天数着日子过,天天算着什么时候放暑假,什么时候放寒假,什么时候开学,因为儿子一开学就是一万多。他没有别的大本事,只能在建筑工地上出苦力。他像小时候一样,天天盼着过年,因为过年他就可以见到儿子了。可是到了过年的时候他又决定不回去过年了,留在工地看场子,既不出力又比平时多拿工资,就这还没人愿意干。别人不干他干,因为他比别人更需要钱,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还债。这样,虽然失去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可是他一算账觉得还是划算的。过年要是回家,不但不能挣钱,人情往来还得花钱,一进一出差好几千块,为什么要回家呢?好在现在通信方便,人不回去,打个电话就可以说话了,跟见面差不多。这年,三十晚上他接到儿子的电话,只说了一句:“儿子,爸爸想你们啊!”然后便哽咽起来,泣不成声。
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和弟弟明年就毕业了。等我们毕业了,你就不要再出去打工了,我们的苦日子也快熬到头了。”儿子在电话里说些安慰话。
可是无论儿子怎么安慰,他只觉得心里的悲苦一阵阵往外翻卷,他想笑可就是笑不出来,他不想哭,可是眼泪止不住往下掉。过了好长时间,终于听到了老婆的声音:“你这个没出息的货,大年下,孩子给你打电话,你哭个啥!挂掉吧,一句话不说,白浪费电话费。”随即电话就挂断了。虽然她一直怕老婆,经常挨老婆的训斥,早就习惯了,可是今天他还是感到老婆的话有点不近人情。嘟嘟的电话忙音灌入他的耳朵,他握着手机在那里愣神,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在这个建筑工地上一连干了几年,年年想着回家过年,可是一直也没能回去过一次年。他天天想见儿子,可是自从两个儿子上大学走后,也总没能见上儿子一面,这让他感到悲凉。不过经过几年的努力,吃苦受罪,他不但可以按时给儿子打去生活费和学费,还把欠下的债全部还清了。他打算今年再干到年底,攒下一二万多块钱来,就回家开开心心过个团圆年。整整四个年头他都没回家了,今年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了,因为大儿子过了春节就要找地方实习了,二儿子说要考研究生,老师说他潜力很大,让他报考上海复旦大学的现代信息技术工程研究生。儿子说:“这是门新兴科学技术,研究生毕业挣钱很容易,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目前IT行业缺人才,工资很高。”
儿子有上进心,有理想抱负,他当然要支持。他想,现在自己还能干,再打几年工,供儿子读研也应该没大问题。他为能有这样的儿子高兴,为此就跟着别人信佛。他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都是菩萨保佑的结果。
天阴沉沉的,漫天的雾霾席卷空中,城里人出门都戴口罩,建筑工地上更是沙土飞扬。刘文革仍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上工。一栋新大楼刚盖到六层,浇混凝土昼夜作业不能停,他一边干活一边计算着回家的时间。腊八已过,还有十几天工地就放假了,浇了这一层混凝土就歇工。他今年无论如何也不再留下来看场子了,他也要像别人一样回家过个年,和老婆孩子一起吃个团圆饭。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有一股冲动,顿时一股暖流灌注全身。一股呛人的灰尘吸进来,他立即一阵猛咳,忽然他脚下一滑,一个趔趄,然后一脚踏空,“哗通”一声摔了下去......
等他醒过来,已经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吊水瓶里的盐水咕嘟嘟冒泡,一滴滴水落到软皮管子里输到他的血管里。他的胳膊和腿都打着绷带,守着他的工友告诉他说:“你一跤跌了下去,摔到脚手架上,多处骨折。幸亏有安全网,才没有摔到地上去,要是落在地面上,你肯定就没命了。你没伤着内脏,骨折养段时间就能好,因此你也不要难过。你真是命大啊!看来是你信佛起了作用了。”工友说罢就嘿嘿一笑,接着问:“你看要不要通知你家人,让你老婆过来照顾你几天。”
“不用,不用,”他头上缠着绷带,说话不清楚,一句话没说出来,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他皱着眉头,强忍着。他想说句感谢的话,可是说不出来,浑身都疼,疼得钻心。一股巨大的悲哀涌上心头,两行眼泪又控制不住流下来......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
责任编辑:孙克攀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 活动报名/会员申报 | 证件查询 | 书画商城
网友点评